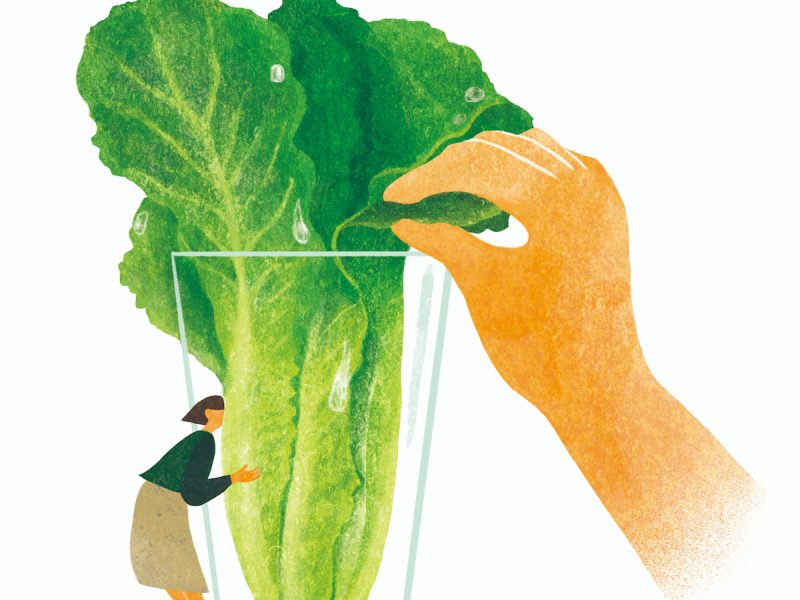藝文
臺灣人熱愛在人行道或公園的樹上寄養自己的綠色寵物,我不知道他們是在什麼時間點把自己的寵物綁上去的,也許是夜黑風高的晚上,也許是清晨甩手操做完之後,總之許多公共空間裡的樹經常懷抱養子,像鯨魚豢養藤壺。
我本人是臉書粉專「田文社」(駐點宜蘭深溝村之農業報導網站)的忠實粉絲,如果你也像我一樣三不五時巡水田一樣逛田文社,就會知道他們的吉祥物(?)乃粉紅色的福壽螺卵,田文社除了推銷地方農產、介紹悲喜交織的務農實況,也賣繡有「螺福宮」的粉紅棒球帽、福壽螺卵紋身貼紙、「歡螺喜穀」福壽紅包袋等周邊產品,讓人時時刻刻記得福壽螺卵對臺灣農民來說是多麼難纏的角色。
Discovery頻道《漁人的搏鬥》(Deadliest Catch)記錄阿拉斯加捕蟹船的討海生活,無論在收視與評價都是真人實境秀領域的翹楚,數以千萬人都曾透過它隔空領略過白令海峽的殘酷,此秀自2005年開播至今洋洋灑灑過了18季,養一個孩子都可以上大學了。
記得2022年金門大橋剛開通沒多久,11月初我便跟著朋友到小金門夜遊。晚間9點多,整座小島就已進入休眠狀態,我們穿越了長長的黑暗,直到西方村眼前一亮,許多村民聚在廟旁聊天,戲臺上的包青天正演得熱烈。
每到芒花盛開的季節,就是賽夏族連續三夜的矮靈祭登場之時,今年在北賽夏舉行,我跟朋友在第一晚上山,頭一件事就是到祭屋報到,讓族人繫上避邪的芒草。繫上後,彷彿勾勾手做約定,與賽夏族一起遵守祭典規矩。
身邊許多男性同儕迷戀K-POP舞臺上那些鉛筆腿的熱舞女團,長期以來我隱約能感受到K-POP無遠弗屆的規模與威力,即使輕度臉盲症患者如我至今仍無法辨識其中任何一位巨星。
提到火車,你首先聯想到什麼呢?是朱自清爸爸的橘子、慈母為入伍兒子準備的鐵牛運功散,是林強的〈向前行〉,還是近日重登大螢幕的磅礡史詩電影《齊瓦哥醫生》?火車與驛站送往迎來,見證了現代文明與個人生涯中各種糾結的時刻,生離死別,戰爭與移民。
年初,我在家附近的銅錢草叢上看到一隻小蝶,顏色像剛破曉的冬日天空,迷濛的淡藍透紫,不比一元銅板大。我特地拍照,過一陣子找來徐堉峰所著的《台灣蝴蝶圖鑑》灰蝶專冊比對,發現它是灰蝶科(英文暱稱為Blues)中的「藍灰蝶」。翻閱圖鑑之後,才知道這種蝶類的中英文泛稱並不能展現其多樣性,牠們經常不是藍也不是灰,背、腹面的翅膀顏色與花紋也有戲劇性差異。
不久前順遊雲林與嘉義沿岸,是為了看一眼反覆出現在電影中的奇幻水鄉。黃信堯的紀錄片《帶水雲》採集雲林口湖風景,此地與陳玉勳的《熱帶魚》、《消失的情人節》拍攝地點嘉義東石相連,這片腹地百年前是潟湖,之後拓荒成良田,近40年因超抽地下水與海水倒灌,良田再度被上天收回,現今四處都是水淹民居、馬路與電線杆一截截沉入海中、海邊枯樹敗倒的超現實畫面。
年幼時,我曾跟隨表哥到阿嬤家附近水圳釣魚,有樣學樣地做了一根自製釣竿,釣線另一頭綁的是虛擬魚餌:一顆鈕扣。我的表哥長大後依然熱愛釣魚,他曾經半夜和一群漁友搭小船前往外礁海釣,漲潮的時候礁島表面積漸漸縮限得剩下一張地毯那麼大,一群漁友就這麼無路可退地於暗夜中垂竿,破曉時船老大才返回孤島接他們回家。
5月,臺中科博館BRT候車亭頂棚出現六隻恐龍,古典筆觸與柔美色調出自於臺灣繪者鄒駿昇之手,一掃過往恐龍(以及臺灣各種為了翻新而粗製濫造的彩繪)視覺上經常帶給人的暴烈與壓迫感,在我看來是一次相當成功的地景改造。
2009年,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過一場電影導演提姆‧波頓(Tim Burton)的漫畫特展,波頓原本是迪士尼的畫師,後來轉行成導演,擅長打造復古、憂鬱、哥德式冒險的異想世界,當時他已經是好萊塢的明星導演之一,此前他的《剪刀手愛德華》、《蝙蝠俠大顯神威》、《地獄新娘》等一長串作品已經是談及美國通俗片史時完全無法繞過的障礙,簡而言之,「提式風格」已經是一種文化現象,有看電影習慣的一般大眾可以豪不費力地把它當成共通話題。
今年臺灣書市出現了兩本關於雪豹的作品,一本是臺灣作家徐振輔的《馴羊記》,一本是法國作家席爾凡.戴松(Sylvain Tesson)的《在雪豹峽谷中等待》(La panthère des neiges),風格南轅北轍,為這半個世紀以來以追尋雪豹為主題的創作增添了有趣的兩筆記錄。
許久前我在電視上看到一部短片,國外一間名為Whooshh Innovations(意指「咻一下飛過去新創公司」)的單位發明了一種名為「鮭魚大砲」的東西,這條管子長得像一條架在山川之間的超大型吸管,用以幫助那些在下游焦慮徘徊、力爭上游的鮭魚抄捷徑,省略好幾天的洄游過程,以「搭高鐵」的方式瞬間空降到上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