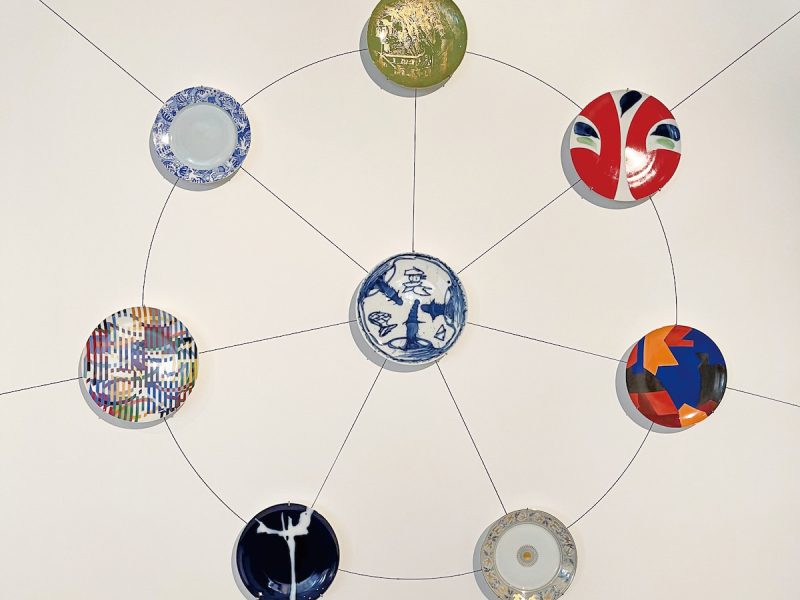飲食
回想年幼時常泡在圖書館,其實不怎麼專心讀書,一心等待下午2點就會出現在圖書館旁的雞蛋糕攤車。許多人應該都跟我一樣,在那喊著「媽媽給我十塊錢」的年紀,一包雞蛋糕就是最奢侈的甜點時光。雞蛋糕對我、甚至對大多數臺灣
人而言,絕對是臺灣小吃的經典之一。
出了東門捷運站一號出口,右轉便是小販簇擁的臨沂街。街販漫進巷內,不留神就會錯過裡頭一座公園,更不會發現公園中還藏有兩間小廟,其中田都元帥廟對聯寫著「善惡入門神先奉,見吾不拜也無妨」, 元帥真豁達。。
民以食為天,無論到哪個地區,總要嘗一嘗在地料理,試圖透過味蕾感受當地的風土特色。上網搜尋維也納必吃甜點,第一名是烏漆墨黑的薩赫蛋糕(Sachertorte)。它是一種外觀樸素、缺少裝飾的巧克力海綿蛋糕,內部夾入一層杏桃果醬,外頭再覆蓋巧克力糖霜,做好以後要先冷藏三小時讓糖霜變硬,上桌前在餐盤邊擠一坨鮮奶油陪襯。外型看似簡單,製作卻意外困難,傳統作法共有36道步驟,光是外層糖霜就必須混合四種巧克力,不僅食材工序講究,連每日環境溫溼度都是變因,必須謹慎考量。
涼麵,大概是臺北這個夏季炭盆中,最令人感到舒適的宵夜。記得老遠以前,我初登社會職場時,不知道哪裡來的莫名執著,鐵了心要待在扣完房租和生活費後,幾乎所剩無幾的臺北;經常在忙碌到大半夜後,抵不住餓意侵襲,就順手牽輛YouBike,穿梭在臺北市房價最高的區域,尋找平價涼麵的蹤跡。
聊起馬賽,你第一個會想到什麼?如果閱讀旅遊指南,通常會介紹馬賽是擁有沙灘遊艇、海鮮美食、熱情包容的地方,也是南法普羅旺斯的最大城鎮。最著名的景點,莫過於建在石灰岩峭壁上的守護聖母聖殿(Basilique Notre-Dame de la Garde),它是羅馬天主教宗座聖殿,居高臨下俯瞰並保護在馬賽老港(Vieux-Port)生活的討海人,還有被評為世界三大湯頭之一的馬賽魚湯。
說到意麵,你腦中浮現的是什麼畫面?我猜,大家現在腦中的畫面肯定不盡相同。於我來說,在幼年仍懵懂的時期,心中對於意麵的印象,就是在新竹一方小店裡,有碗透著油光的縷縷細長白麵,淋上肉圓或是蚵仔煎都通用的紅色醬汁,緊緊依附著麵條,還必得配上一碗貢丸湯,方成大局;於大部分臺南人,甚至絕大多數的南部朋友而言,鹽水意麵大概是意麵派系中最廣為人知的代表。
朋友一日午後到新化走踏,發表了「新化好好逛」一說,因為老街上有巴洛克式街屋群、日治時期的古蹟、文學館、故事館,以及地瓜餅,朋友大概沒想到,老街的後方,在晨間是一大片台式食貨交易場,也「好好逛」啊。新化市場除了主體建物外,街販又沿著信義路及其兩側巷弄蔓生到一公里外的大街上,遙望不見底,忍不住在午後大雨前的熾熱發起牢騷:「也太長了吧!」
作為一個善化人,善化菜市場,我可真不熟悉。過去的我幾乎不曾佇足市場大樓的一樓攤位區,我只知道,二樓聽說有鬼,搭電梯要小心別按到「2」,三樓是圖書館,四樓是舞蹈教室,五樓有全聯。以前平均每週有三天要到四樓跳舞,國三以後,天天要上圖書館K書,好不容易考上了高中,迎來的竟然又是,連續三年放學後,回到以為能夠遠離的圖書館。
「基隆限定」這四個字,幾乎成為了蛋腸專屬的廣告臺詞。我與蛋腸的初次見面,是在近十年前於臺北劍潭附近,有一家名為「富樂」的甘蔗小火鍋店,我想這家店應該是大部分的士林區居民都會推舉的名店,除了高性價比的餐點、多樣豐富的飲料冰品之外,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會隨菜盤附上的基隆手工蛋腸。
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、立陶宛,這三個名字像童話故事般夢幻的國度,因位在波羅的海旁邊,統稱為波羅的海三小國。自古以來,他們的國力沒辦法強大到成為統一的文化,在列強圍繞下常被逼著依偎不同的大西瓜,近代歷史上先被俄羅斯帝國收編,一度獨立又被納粹德國占領,二戰後再成為蘇聯的附庸國,長期被強權擺布,活成別人要的模樣。1989年8月23日,兩百萬居民手牽手,從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,排排站到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,連結出快七百公里長的人鏈,這個稱為「波羅的海之鏈」的和平示威活動,宣誓了三小國的獨立性與民族認同。
每個歐洲人心中都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愛爾蘭酒吧。石瓦堆砌的復古老建築,門口掛上綠色四葉幸運草的招牌,遠看像是矮人地精會出沒的場所……走進店內別有洞天,愛爾蘭風笛的背景音樂中有踢踏舞的節奏,上百種眼花繚亂的酒款、酒瓶、玻璃杯整齊堆滿櫥櫃,燈光昏暗但氣氛溫暖,一團團顧客沒有你我他之分,隨興的從這桌聊到那桌,友好且歡樂,每個人都能在這找到自在的歸屬。
「選——麵筋,吃麵筋,吃——麵筋,好腦筋,選——有土豆的唷!」不曉得各位現在腦中是否浮現藝人胡瓜青澀的臉龐,搭配著這段無比洗腦的廣告歌曲,與兩位小孩在畫面中蹦蹦跳跳搶吃麵筋的畫面?沒錯,這是早期愛之味麵筋的經典廣告。後來,也許是礙於食品法規的因素,「吃麵筋好腦筋」的廣告詞不復出現,但麵筋配稀飯的習慣,早已成為臺灣人最樸實無華的早餐組合。
在這疫情當兒,大家小心翼翼、減少出門、避免外食,平時兜不在一起的室友們,終於受夠了各式自製沙拉和料理包快餐,三人相約來煮一頓豪華的。平時不怎麼下廚的我,也不願在室友面前丟了臉,早早宣布要來一道冰糖醬燒排骨,讓自己後悔也來不及。問題來了,這排骨去哪生呢?我們避開連鎖超市,踏進久違的菜市場,幸好,人在宜蘭五結鄉利澤村,人口不過兩千多,市場也因疫情少了許多攤販和購物人潮,放眼望去冷冷清清,難形成群聚。
我好喜歡吃鰻魚,想必很多臺灣人也喜歡這甜甜鹹鹹的滋味吧。鰻魚最早記載於奈良時代(710至794年)的書裡,但沒有寫到烹調方式。此後日本各地便出現多種吃法——切塊後串燒鹽烤,加味噌或蘸醋調味等,據說當時認為鰻魚是一種「營養豐富但不好吃的魚」。
每年4、5月之際,春風正盛,陽光仍舊曖昧,不至灼熱,我習慣安排一趟小旅行,沿著北海岸走走——觸摸白沙灣細膩的沙,欣賞老梅石槽深邃的綠,聆聽海洋拍打的浪,讚嘆野柳自然藝術的岩,最重要的莫過於來杯石花凍,鎮壓在都市裡繁忙的慌。
家住臺南善化,南鄰新市,即使不常造訪,它卻一直以各種樣子存在我的印象中,從小時候爸爸三天兩頭說:「我要去新市買冰鎮滷味!」到高中搭火車上學,「新市站到了」,這個令睡不飽的學生感覺啊雜的機械式報站女聲,到後來南部科學園區蓋起,當年的國中小同學一一前往新市上班。這個伴我左右的地方,在我大學離開臺南後,卻成了極少人聽過的地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