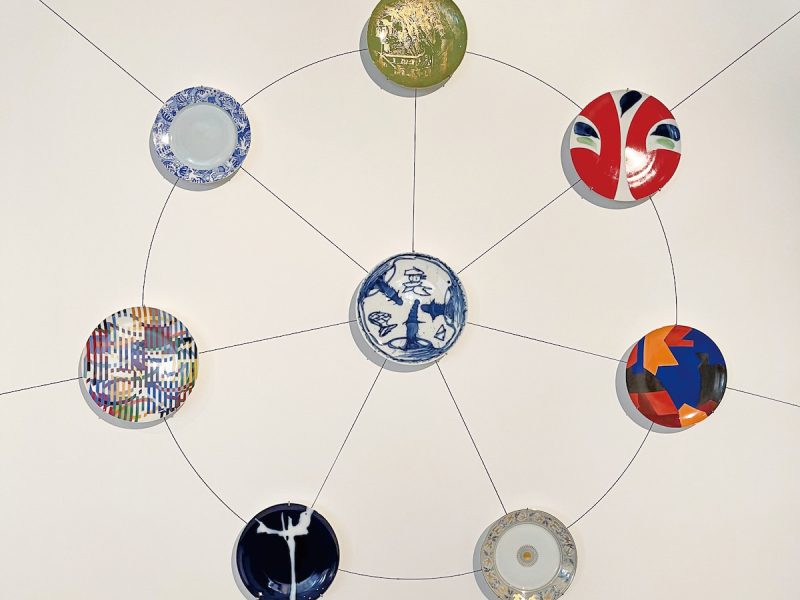飲食
在我家,到魚市場買魚是父親的差事。難得回家一趟,某次我隨口嚷嚷著,也想到魚市場逛逛,隔日時針才剛走到五,房外便傳來父親催喊:「再不出門,好貨都要被挑光啦!」
澎湖人買魚,除了到北辰市場,大多還會起個透早到第三漁港的澎湖魚市場搶鮮。因應漁業型態的轉變,第一、第二漁港在二〇〇二年從傳統漁港轉型為觀光休閒漁港,目前馬公市區則由第三漁港繼續發揮著漁獲集散的功能。
王俊智是我大學的同系學長,只大我一屆,但直到畢業前,都不知道他家裡是種茶的。
俊智聽了大笑說,有啊他有介紹過,「大學生沒有人在喝茶的啦。」他說。
我們約在梅山交流道附近會合,俊智與他爸媽開車帶路,他們家在雲林古坑跟梅山交界的龍眼村金鳳寮,海拔將近一千。下車後,很快看到俊智媽媽照料的菜園。她說太忙沒空收成,有要煮才會過來採。說著就採了幾顆燈籠果的果實給我吃,很香甜。我們從家旁的單軌車上山爬坡,進入茶園。
最近朋友很愛講起「富貴雙全」這個字。
雖然老大單身,跟在婚姻內拖磨的其他友人相比,竟發現原來一個人的日子,過得是既清省又自在。而那自在,比起婚姻關係中的種種蹇滯難行,來得快活太多了;中年後眼界開了,才發現富與貴二字,不能只局限於物質層次。看似人生走得庸庸碌碌,剛繳清了學貸,隨即又開始和大家一起背車貸、房貸,但能在生活的狹窄中脫身,在心境上也擁有大坪數空間,才真正是得了個富貴雙全。
全國一年就喝掉約新臺幣五百三十八億元的手搖飲,高雄跟臺南包辦了其中的一百六十億元,儼然是臺灣的國飲,其規模與商機不容忽視。
一家手搖飲店平均有四十種以上的品項,這些品項多由茶、奶、珍珠等幾樣基本元素,經過各種排列組合而成,更要求新求變,以滿足無止盡的新鮮感。隨時代進步,有店家開始講究茶葉,標榜產區、茶葉品質、萃取方式;或從配料下手,椰果、粉條、布丁等,越摻越花俏。
在英國,尤其是英格蘭地區,每到星期天許多餐廳與酒吧都會供應星期天烤肉(Sunday roast)。這是一整盤由牛、豬、羊或雞肉,加上兩三種蔬菜(通常是紅蘿蔔、高麗菜與馬鈴薯),與蓬鬆柔軟吸肉汁的約克夏布丁(Yorkshire pudding)組合成的豐盛料理。既然都叫烤肉,顧名思義肉類都是烤製而成,配菜有時水煮有時一起烤製,並一定會淋上肉汁。
英國的烤肉相比臺灣路邊炭烤或是桶仔雞,顯得秀氣,直白一點也可說是清淡。
我出生以前,爸媽曾住在三民街附近,我卻遲至年近三十,才發現它的好(吃)。
傍晚,來到這當地人都親暱稱它「三民街仔」的小路,兩側攤販排得滿滿:燒肉飯、燒麻糬、燒馬蛋、意麵、黑輪、蝦仁羹、當歸鴨、粉圓冰、檸檬汁,露天小攤做食物不馬虎,動輒開業數十年,是不少家庭至少兩代人的共享滋味。
賣香菇雞湯的老闆,身材激瘦、頭髮蓬爆,緊身褲與白布鞋,和音響放送的迪斯可舞曲、英文老歌十分搭配。
前往塔塔加的第一天,天氣很好,山上已有管制,因為分岔路通往賞花勝地草坪頭,我們朝另外一條開去,繼續往阿里曼大哥指示的茶園方向前進,結果,一開始就走錯路。
車辛苦開進高草叢、坡度極陡的山路到達茶園,沒看到大哥,大哥說我們走錯了,跑到對面別人的茶園了,大哥要我們開下山再開過來,又指示了半天,終於走對路,大哥一邊在電話裡鼓勵我們:「加油快到了,我已經聽到你們車子的聲音了。」
臺中有一路一五三號公車,頭班清晨六點,我偶爾會搭這班車到谷關。週末搭這班車的幾乎都是登山客,很快就把整臺車塞滿。他們個個全副武裝,一包一杖,空間感往往比平時更窄小。
別忘了,人之間有一條線,幽微但明顯,無形卻燙手。
偏偏登山又有一種奇妙的效應,會讓邂逅的人模糊那條劃分距離的線。
那天我要走德芙蘭步道上東卯山。坐在靠窗位置,背包放在大腿上,鄰座是位目測六十歲左右的大哥。
春天是菜蔬極美的季節。草木萌芽,葉菜類紛紛開花,二月到四月正值芥藍花上市,一大把賣五十元,能吃好幾餐。
小時候只知芥藍炒牛肉好吃,卻不知道芥藍花也可以吃。有一次跟父母去鄉下,採回一大把盛開的白花芥藍,美極了,草花有一種恣意的生猛氣勢,抽高的花梗上星星點點,素樸又聖潔,怎麼大家沒有想到可以栽培來做裝飾用切花呢?
一次,在大學裡講關於白粥的飲食文化,學生們一臉茫然,彷彿我講的是天方夜譚,只有隨堂老師很有共鳴地說:「有有有,我們家就是這樣吃。」
我忍不住問了其中一位學生:「你上次吃到白粥是什麼時候?」他回答:「三年半前,在阿嬤家。」我又問:「你吃到什麼配粥菜?」他回答:「罐頭蔭瓜、肉鬆跟皮蛋。」我再問:「你今天早餐吃什麼?」他回答:「雞米花、蛋餅跟奶茶。」
這幾個回答透露著許多資訊,現代人飲食西化,白粥已非一般人日常。
七年前我隻身一人來到倫敦讀書做研究。初來乍到,對當地飲食地景還是一張白紙,街道上的各式連鎖超市與咖啡店名,對我來說都是新奇異域。在一片矇中,我漸漸能識別一些高出現率的店家,其中第一個認識的就是「Pret A Manager」。Pret在英國算是最常見的連鎖咖啡店,鬧區每三五步就能見到一家。
Pret專門賣咖啡、三明治與一些甜麵包或酥餅,以連鎖店的品質來說,用料與賣相算是非常不錯,便利與健康兼具。
對這張手繪薑母鴨看板按下快門的瞬間,我想起自己幾年前用一樣的角度拍過這攤位,「阿姨妳以前是不是賣過蓮藕?」過去看板上,阿姨自己畫了一條蓮藕,筆觸稚嫩而韻味十足。如今她改賣薑母鴨,「這隻鴨是我未來的媳婦畫的。」從蓮藕到薑鴨,有愛情正發生。
再次來到這兒,為的是帶小學生逛市場。永康市場對面就是永康國小,學校因此將只隔了一條馬路的市場納入教育範圍,邀請相關主題寫作者引領學生進市場走讀。
因緣際會下,由前輩老師們的帶領,我們一行人來到張弘陸老師的個人空間。沿著坡邊有幾棵芭蕉,已按鈴等待的我們,透過芭蕉,指認後方樹林中的幾棵茶樹,遠遠看去,要認葉子都不容易,頂多只能辨認相對位置。張老師前來開門引路,從上石階到入屋,簡直像進入一場時空之旅,還沒坐上茶桌,門口一股幽甜沉靜的香氣,已進入鼻息,有點古意,卻不敢斷言香氣到底是來自哪裡。
我不太懂山產,走在山裡的時候,往往只顧著認路、拍照、管理時間、胡思亂想,根本無暇顧及山道旁長著什麼;即使注意了,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看到什麼。
箭筍可能就屬於這類低調不起眼的山產吧,一株不及一個腳掌高,包覆著青中帶紫的外皮,藏在茂密的竹林裡,混雜在枯枝落葉中,我這種山產麻瓜根本認不得。
但那次登西巒大山的箭筍採集之旅,確實是一次難忘的經驗。
屏東飯湯的靈魂是用油蔥酥、泡好的乾香菇、蝦米爆香,炒到香氣飽滿後才加入水熬高湯,最後點睛之筆,是撒上芹菜珠或香菜。至於用料各地皆不太相同,市面上最常見除了肉絲、筍絲,還會放點紅蘿蔔絲、高麗菜絲增加鮮甜,再放幾顆貢丸、魚丸、幾尾蝦子,將味道層次再提升。
茴香在翻譯世界裡,一直是個撲朔迷離的存在。
小時候讀杜瑞爾的希臘旅居記述,裡面提到一種茴香酒「烏佐」(Ouzo),酒色清澈透明,但是只要兌入冰水,整杯酒就會變成如雲朵般乳白。地中海區域許多國家皆生產這種茴香酒,如土耳其生產的拉克酒(Raki)、敘利亞區域的亞力酒(Arak)等。這種酒是在派對歡聚時候飲用的,通常搭配各種冷盤小點,邊喝邊聊。對於地中海居民來說,一起飲用烏佐酒算是某種友誼儀式,代表接納、聆聽與愛。
朋友說要年終聚餐,請我推薦好吃的烤鴨名店給他,我問:「要吃北京烤鴨還是廣式烤鴨?」他說:「有差嗎?」有喔,很不同,在臺灣同時能吃到北京燜爐烤鴨跟廣式片皮鴨。
香港傳統粵菜吃「燒鴨」。把烤好的鴨斬件,一隻鴨斬成五、六份,燒鴨是烤鴨,但不是北京烤鴨,北京烤鴨有專有的作法、烤法、片法跟吃法。
位在倫敦西區,具有久遠歷史的英國早餐店Regency Cafe,每到假日,外頭必定排了長長人龍,不分觀光客還是英國在地人,都在隊伍中等著吃上一份英式早餐。復古氛圍的店裡瀰漫著煎蛋、濃茶與煎肉的氣味,精神颯爽的老闆娘聲如洪鐘,喊著客人來拿餐,一邊俐落的倒茶、抹吐司。
比起下午茶的精緻,英式早餐多了一股粗獷,但又具有獨特美感。現今廣為熟知的英式早餐,是廿世紀之後才漸漸標準化的菜色,在那之前,吃一頓精美早餐是仕紳或上層階級較為熱衷的活動。
對於想吃蛋捲又怕胖的人而言,米蛋捲具有心理上的安慰作用。
然而米蛋捲生產者普遍為自耕小農,於是這「水花園有機農學市集」,成了氣溫十一度的今天,讓我踏出門的理由。經歷了幾次搬遷,市集今年落腳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,一眼可見盡頭的攤位數量,卻讓我在離開時候,驚覺已過三小時,並且獲得三次滿額抽獎機會──原本不是只打算買一桶蛋捲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