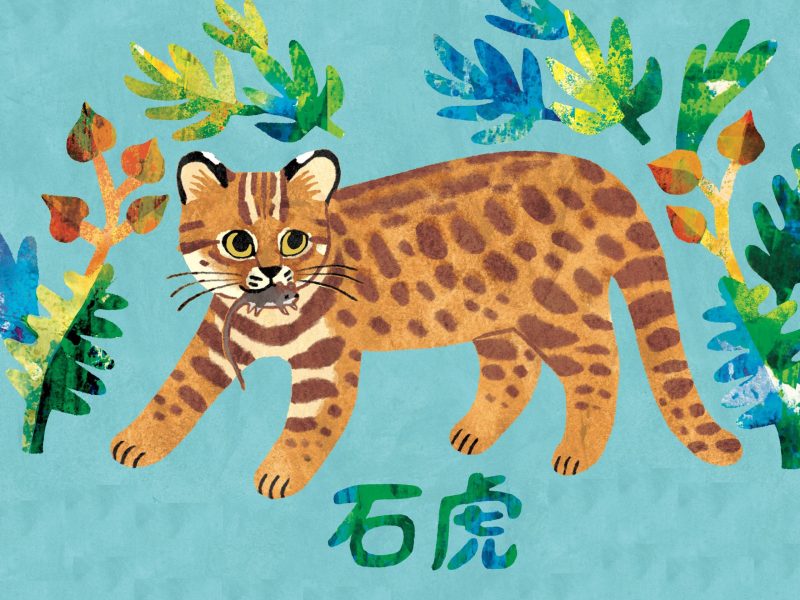土地
澎湖人對於神靈的崇敬,從日常生活中的「石敢當」就能窺見一二。
老一輩的人敬天尊地,常以信仰的神靈作為規範行為的準則,漸漸養就人們對未知的恐懼,與敬畏大自然的態度。在澎湖四面環海、冬季風大浪高的特殊地理環境中,石敢當的存在,便是幫人擋去災厄。從現代角度來看,晚上太黑怕出門會危險,所以警告「亂跑會被鬼抓走」;冬天風大要小心,便在風口處建石塔提醒人們當心;不希望村民跑離村里太遠遇險,就在四周建造「五營」限定範圍等等。
自古蓋廟靠勸募,然而跟著白沙屯媽祖進香居然被「勸吃」,若不加以說明的話,大概要以為來到哪個夜市一路被推銷。
白沙屯媽祖年年到北港進香,據新聞報導,今年跟著「粉紅超跑」走的人特別多,將近十八萬人報名香燈腳(白沙屯拱天宮對進香信徒維持的傳統稱呼),創歷史新高。加上其他跟著走的信徒,一起跨越苗栗、臺中、彰化、雲林四個縣市,粉紅炫風帶起的流動實在很驚人。
前往塔塔加的第一天,天氣很好,山上已有管制,因為分岔路通往賞花勝地草坪頭,我們朝另外一條開去,繼續往阿里曼大哥指示的茶園方向前進,結果,一開始就走錯路。
車辛苦開進高草叢、坡度極陡的山路到達茶園,沒看到大哥,大哥說我們走錯了,跑到對面別人的茶園了,大哥要我們開下山再開過來,又指示了半天,終於走對路,大哥一邊在電話裡鼓勵我們:「加油快到了,我已經聽到你們車子的聲音了。」
臺中有一路一五三號公車,頭班清晨六點,我偶爾會搭這班車到谷關。週末搭這班車的幾乎都是登山客,很快就把整臺車塞滿。他們個個全副武裝,一包一杖,空間感往往比平時更窄小。
別忘了,人之間有一條線,幽微但明顯,無形卻燙手。
偏偏登山又有一種奇妙的效應,會讓邂逅的人模糊那條劃分距離的線。
那天我要走德芙蘭步道上東卯山。坐在靠窗位置,背包放在大腿上,鄰座是位目測六十歲左右的大哥。
連假期間,和友人們討論要不要去爬山,扔了兩座山進群組,一座是東眼山,一座是法鼓山;考慮到連假過後的開工,大家決定一起上法鼓山走走,感覺爬完腳不會太痠痛,是個放鬆的健行行程。
雖然我家在三芝山上,也一直聽聞過法鼓山,但從沒去過;剛好友人認識法鼓山的師父,就帶我們一起上山去走走了。
上山之前,我就聽過法鼓山長期推廣「植存」,想想,自己也來到經歷越來越多離別的階段,去預先做點功課也好。
七年前我隻身一人來到倫敦讀書做研究。初來乍到,對當地飲食地景還是一張白紙,街道上的各式連鎖超市與咖啡店名,對我來說都是新奇異域。在一片矇中,我漸漸能識別一些高出現率的店家,其中第一個認識的就是「Pret A Manager」。Pret在英國算是最常見的連鎖咖啡店,鬧區每三五步就能見到一家。
Pret專門賣咖啡、三明治與一些甜麵包或酥餅,以連鎖店的品質來說,用料與賣相算是非常不錯,便利與健康兼具。
對這張手繪薑母鴨看板按下快門的瞬間,我想起自己幾年前用一樣的角度拍過這攤位,「阿姨妳以前是不是賣過蓮藕?」過去看板上,阿姨自己畫了一條蓮藕,筆觸稚嫩而韻味十足。如今她改賣薑母鴨,「這隻鴨是我未來的媳婦畫的。」從蓮藕到薑鴨,有愛情正發生。
再次來到這兒,為的是帶小學生逛市場。永康市場對面就是永康國小,學校因此將只隔了一條馬路的市場納入教育範圍,邀請相關主題寫作者引領學生進市場走讀。
澎湖四面環海,漁業是早期居民的重要生計。而媽祖娘娘作為「海神」,自然成為澎湖漁民最崇拜、最信仰的守護神,就連市區地名也是因為坐鎮了「娘媽宮」而被稱為媽宮,繼而演變為馬公。
原先的媽祖宮曾經遭受荷蘭軍隊毀壞,但信眾們隨後齊心重建。康熙年間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帶軍來到澎湖,認為媽祖顯靈助其獲勝,所以奏請朝廷加封為「天后」,從此媽祖宮成為享有「每歲三祭,物用太牢」的廟宇,並更名為「天后宮」沿用至今。
到日本大阪旅行的時候,正好遇到「四天王寺」每月二十一與二十二日才有的集市,於是選日不如撞日造訪四天王寺。四天王寺在日本佛教史上地位重要,擁有三個甲子園大的面積,匆匆來去是逛不過癮的,我在這裡意外發現工匠與他的守護者。
西元五九三年,聖德太子創建四天王寺,本尊觀音菩薩,配祀四大天王,是日本佛教最初的官寺。說起聖德太子,到過日本旅行的人應該都不陌生,他被印在上一代萬元日鈔上,是重量級人物。
我不太懂山產,走在山裡的時候,往往只顧著認路、拍照、管理時間、胡思亂想,根本無暇顧及山道旁長著什麼;即使注意了,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看到什麼。
箭筍可能就屬於這類低調不起眼的山產吧,一株不及一個腳掌高,包覆著青中帶紫的外皮,藏在茂密的竹林裡,混雜在枯枝落葉中,我這種山產麻瓜根本認不得。
但那次登西巒大山的箭筍採集之旅,確實是一次難忘的經驗。
屏東飯湯的靈魂是用油蔥酥、泡好的乾香菇、蝦米爆香,炒到香氣飽滿後才加入水熬高湯,最後點睛之筆,是撒上芹菜珠或香菜。至於用料各地皆不太相同,市面上最常見除了肉絲、筍絲,還會放點紅蘿蔔絲、高麗菜絲增加鮮甜,再放幾顆貢丸、魚丸、幾尾蝦子,將味道層次再提升。
茴香在翻譯世界裡,一直是個撲朔迷離的存在。
小時候讀杜瑞爾的希臘旅居記述,裡面提到一種茴香酒「烏佐」(Ouzo),酒色清澈透明,但是只要兌入冰水,整杯酒就會變成如雲朵般乳白。地中海區域許多國家皆生產這種茴香酒,如土耳其生產的拉克酒(Raki)、敘利亞區域的亞力酒(Arak)等。這種酒是在派對歡聚時候飲用的,通常搭配各種冷盤小點,邊喝邊聊。對於地中海居民來說,一起飲用烏佐酒算是某種友誼儀式,代表接納、聆聽與愛。
澎湖寬廣的潮間帶是居民「靠海吃海」、與大海共生的地方。這片富饒的海域至今還存在著一種較無侵略性、利用潮汐漲退「請魚入甕」的捕魚方式──「石滬」,不但見證了澎湖漁業的興盛與蛻變,也成為澎湖極具代表性的文化遺產之一。
石滬為利用石頭所堆起的捕魚陷阱。通常是漁人們觀察潮汐和水流的方向後,再以玄武岩、咾咕石順應地勢堆砌成彎延長牆。
數大就是美,在府城「普濟燈會」可以得到印證,一千八百盞燈籠高掛在「普濟殿」廟埕與國華街上,鋪成一條長長的天空燈河,路過的人仰著看、笑著看,從心底「哇」出來地讚嘆。普濟燈會很美,美在為數眾多的燈籠,也美在匯聚夢想的放光。
位在臺南中西區的普濟殿,距今有三百多年歷史,是臺灣最早的王爺廟。對外地遊客來說,普濟殿是一年一度看燈會拍美照的景點;對府城人來說,在歷史和地理上,更是舉足輕重。
「綠光農園」的店面位在北勢溪上方的商家街道,陳大哥與太太熱情招呼我們。一進門,就看見地板上起炭的火盆,在茶桌旁坐下,絲毫不覺冷。外頭洶湧的溪水聲頻頻入耳,氣勢不輸瀑布。
我問起綠光的名字,陳太太笑說:「就是茶園的綠色光芒呀!」閒談過程中,聊起綠光農園提供民眾前來體驗的起因,原來是「有機」一詞的過度氾濫,讓他們覺得應該要請大家親自進到茶園來,眼見為憑;且不論是想感受採茶或製茶,都歡迎預約來訪。
配膳是一門藝術,尤其要負責隊伍伙食的時候。
你要計算食材的重量,詢問大家飲食方面的好惡,設想每個人的分量,照顧好大家爬山的營養、熱量,以及心情。沒錯,心情。讓夥伴吃得開心,可能比什麼都重要。
基於此,伙食在我看來是一件無比燒腦的事,偏偏我又常常是那個喜歡自告奮勇的人。這大概是喜歡下廚的登山人莫名的骨氣吧。
要嚐到檳榔花炒肉絲並不容易,無論是檳榔花或是檳榔心,都極少作為餐廳的固定菜色,即使想買檳榔花回家自己料理,也不像隨時走進全聯掬一把葉菜那樣方便,它伴隨夏天而來,現身在傳統市場裡,在鄉間幹道的路邊攤車,或專營農產運銷的網路門市。
各地都有自己的餃食,或許形狀不同,但都稱為水餃。臺灣早期也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水餃,採用地瓜粉做外皮,包覆蝦米、筍丁與肉末;和現代熟知的麵皮水餃形狀相似,但作法不同,我從小到大也都跟隨長輩的叫法,理所當然稱它為「水餃」。曾幾何時,我心中的水餃被改稱為「水晶餃」,儘管十餘年來我極力試圖為「臺灣水餃」正名,但水晶餃之名幾乎已取代自小熟知的水餃。無奈一道臺灣庶民古早味的水餃,正在我眼前逐漸失真,而我卻無力挽回。
地瓜,也稱番薯或甘藷。在早期臺灣經濟困頓的年代,地瓜曾是農家子弟充飢或餵養豬隻的常用作物,與臺灣農村的命脈緊緊相依。身為農村子弟,「瓜瓜園」的產地經理沈奕岐回憶長輩談起童年的印象,總少不了那道番薯籤永遠比米粒多的「番薯籤粥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