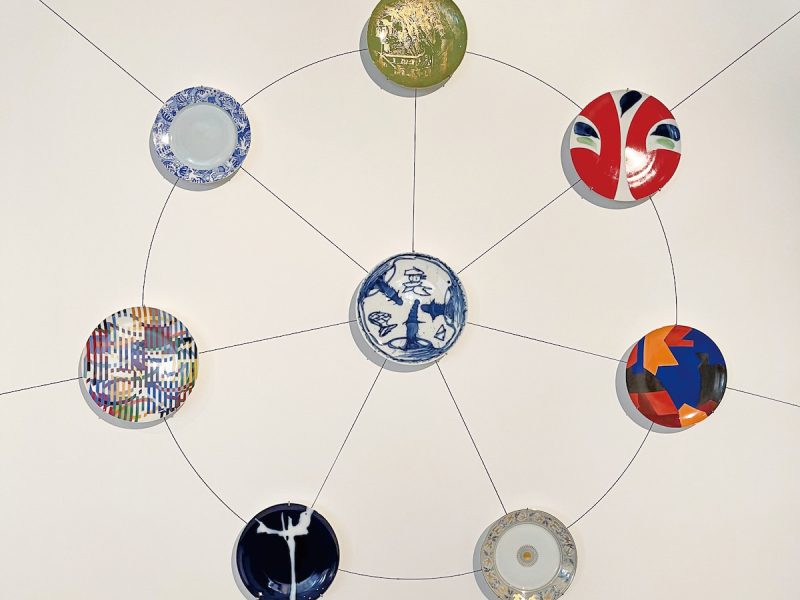飲食
每到炎熱夏天,身體自然就會渴望來杯風茹茶。還記得某年國小暑假全家到西嶼觀光時,正中午被太陽晒昏頭的我直喊想喝冰可樂。「我們小時候哪有可樂可以喝!」父親站在大榕樹下的攤頭前,拿了一瓶黑黑的風茹草茶遞給我,「有井水可喝,頂多熬一鍋風茹加點砂糖,就是人間美味。」
在餐飲業裡,有些人會用自己的名字當作店名,不過王德福恰恰相反。他說:「我是先取了店名叫王德福, 因為諧音像wonderful,好記又喜氣,不過卻無法申請商標,說是要用自己本名才可以,那我乾脆把自己改叫王德福。」
嘴饞,是出發旅行的藉口。「西瓜要採收了,快來吃。」接到小農的通知, 我們一家三口,彷彿家庭公路電影,老爺車引擎轟轟,與此刻的好心情一樣,興奮作響,縱身前往三芝。
除了過年可以領紅包之外,我最期待的節日就是清明連假。不只有兒童節的活動,還有在這個時節才難得能吃到的「大蛤飯」。大蛤實為淺蜊,盛產於澎湖潮間帶,棲息在柔軟的黑沙泥地中,外觀呈長橢圓狀,殼上有明顯的紋路(成長紋),最大可以長到六至八公分,因此被稱作大蛤。
倫敦的夏日水果標配是當季的草莓。這裡的人吃草莓不淋煉乳,除了空口吃,有時候也配點鮮奶油撒砂糖。眾人多譏英國食物貧瘠,但這裡的自產草莓確實香甜多汁且價格不貴。在臺灣長大的我雖非常喜歡草莓,但只有少數時刻有幸食個幾顆;草莓是臺灣冬天的味道,在英國卻是夏日水果,總讓我感到時空紊亂。
當我走進高雄市的海慶澎湖海鮮餐廳時,發現櫃檯旁黑板上寫了密密麻麻的訂位資訊。上面寫著:七美林先生、望安陳小姐、桶盤黃先生等等,我好奇問:「有這麼多來自澎湖各地的人到高雄聚餐?」店家秒解答:「那是包廂名啦。」
曾經,我寫過一篇短文,名為〈最好的咖啡館〉,收錄在我的第一本書中。文章大抵是在說,外出用餐找館子或咖啡館蹓躂時,經常碰壁,得不到滿足,最後選擇回家烤餅乾煮奶茶、與先生回歸居家生活的故事。寫下那篇文章,距離現在已有七年,這七年間我輾轉去了美國與歐洲旅居,小孩也長大到能為我沖咖啡切水果的年紀,再次回到臺北定居,與當初已大不相同。
我自小不愛吃粽子。身為臺灣人,不愛吃粽大概算是異端。我們家沒有親手包粽子的傳統,但從沒少吃過。每到端午前後,冰箱總會塞滿父母各方親友送來的粽子,諸如「母親同事的媽媽親手包的」、「爸爸同事買來的名店」。父母都是愛吃粽的人,不分南北款式全都笑納,獨我看著粽子山是暗暗叫苦,煩惱接下來不知道要連續幾天都吃粽子。
在從前的中國遼寧省遼陽市,有一個大漢左肩架長凳、右肩揹豬肉,沿街喊:「吃酸白菜鍋──」雖這麼喊,但他兜裡才沒有什麼酸白菜,只有一塊四四方方燙熟的五花豬肉,這燙肉會放在木架上塑型成工整樣貌。貧困年代豬肉少,但家家戶戶都有酸白菜,這豬肉便是配鍋必備。
每次覺得蔬菜量攝取不夠時,解決良方就是吃鍋。嬌嫩的葉菜一入滾滾湯汁便姿態放軟,鮮甜可口地在鍋裡閃閃發亮,等待有情人領回。可以大口享用新鮮蔬菜,是我認為一頓大餐該有的重要元素。大約從懷孕後期開始,隨著購買菜量和在家自煮的次數增加,便決定直接訂購每週固定配送到府的時令蔬菜箱。
小時候明明每天吃飯,但對碗裡的米飯一點都不上心。直到某次節食減肥多日,吃了一盒排骨便當,或許是太久沒吃,才終於認識到米飯的好味道。米飯立體又軟Q的口感,可以用筷子夾起來的剛好黏度,再搭配排骨完美平衡的鹹度,那一瞬間我從不識食物滋味、吃飯時如坐針氈只想快點下桌去玩的屁孩,變成愛上食物、每天只期待吃飯的大人。
春寒料峭、乍暖還寒,澎湖的春天偶爾還是會吹起微涼的北風。還記得週末搭晚班飛機回家,頂著寒風鑽進屋裡,正要喊母親一聲時,她早已端著一碗熱騰騰的狗母魚丸海菜湯迎來。母親總是惦記著孩子的喜好,每當知道我要回家後,她便大張旗鼓至市場採買食材,下廚做我愛吃的料理。
近幾年臺灣很流行私廚,有些熱門的店家要隔上好幾個月才訂得到;然而,比起私廚,我認為更難能可貴的是家宴。除了要端出美味的菜色,還得自我揭露,跟大家分享家族中的私密故事。我日前就在新北市華新街一家名為「三季」的預約制餐館,嘗到了以食物為引子的家族遷移故事。
西裝筆挺的年輕小伙子,提著公事包與街口銀色早餐車老闆問早,從老闆手中接過牛皮紙袋,迫不及待地拿出貝果大口一咬。白色奶油乳酪從麵包邊緣溢出,他隨性坐在路旁座椅,享用著熱咖啡,紙杯上頭金色印刷字體寫著──We are happy to serve you.
對廚師來說,每個工作過的廚房都是一個彼時的家。而和家有關的回憶,往往是從一道菜、幾個特別時刻、兩三個人的故事說起。早餐的餐期服務匆匆結束了,負責冷檯早班的S是位白淨高䠷的舊金山小伙子,陽光男孩的笑容帶點迷人雀斑,迎面走向我在地下室廚房備料的工作檯邊,要我張開嘴。
年初失業,憤慨又頹喪地窩在家裡數日,食慾尚在,但就是瞇著眼還看不清目標。這時西班牙友人馬力歐問我要不要春天與他回鄉參加家族大事──表姪受洗禮。原本推託著不要,人生谷底見誰都丟臉。「你來的話帶你去吃便宜又好吃的海鮮。」這時有點動搖,「我們西班牙海鮮比你們臺灣好吃喔!」這下我從病貓變猛虎,氣急敗壞立刻訂了機票,怎麼可能會有比臺灣好吃的海鮮呢,我得親自去吃一趟才有立場辯駁。
疫情期間是馬來西亞小吃店崛起的契機。當時臺灣施行隔離政策,異鄉遊子回不去,想家鄉味都要想瘋了,小店於是一家一家地開。濱城人楊鈦州經營的「爹爹廚房」也在其中之列,不同的是,多數店家選擇開在都會區,他卻開在宜蘭縣冬山鄉。我問他:「為什麼來到冬山?」他說:「這裡像我的家鄉。」
(上篇提要:自告奮勇在英國辦一場臺灣尾牙,沒想到困難接踵而來:20公斤未去毛的生猛豬耳朵、滿滿一箱整隻未剁開的帶毛豬腿以及十幾條完整未處理的魚,到底這場尾牙能否平安度過、化險為夷?)最讓人緊張的當然還是我那一大鍋佛跳牆。在倫敦找不到合適的甕(就算找到大概也沒預算),基於相同理由也省了鮑魚與蹄筋。但我還是找到韓國超市的螺肉罐頭,鹹甜調味吃起來莫名有鮑魚味,拿來代替十分合適。
每個澎湖人心中都有一道屬於自己的療癒食物,對愛吃的我來說,能療癒身心的美食很多──冰花沙拉、海膽炒蛋、蒸蟹、紫菜冬粉等季節限定菜色,就像是餐桌上的風物詩一般,提醒著我四季更迭。不過若要找一個每次回家都一定要吃到的,那就是被我家暱稱「狗蝦炸」的傳統小吃──炸粿。對炸粿這個名詞感到陌生嗎?
周文軍用日本味醂、檸檬烹煮車輪茄,別有一番風味。一提到原住民的食材要素,好像脫離不了阿拜、刺蔥、馬告、羅氏鹽膚木等。那次去嗡嗡私廚,發現他提供的不是過度修飾或誇飾的原住民菜,也不符應外地人的刻板印象,而是如實地彰顯自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