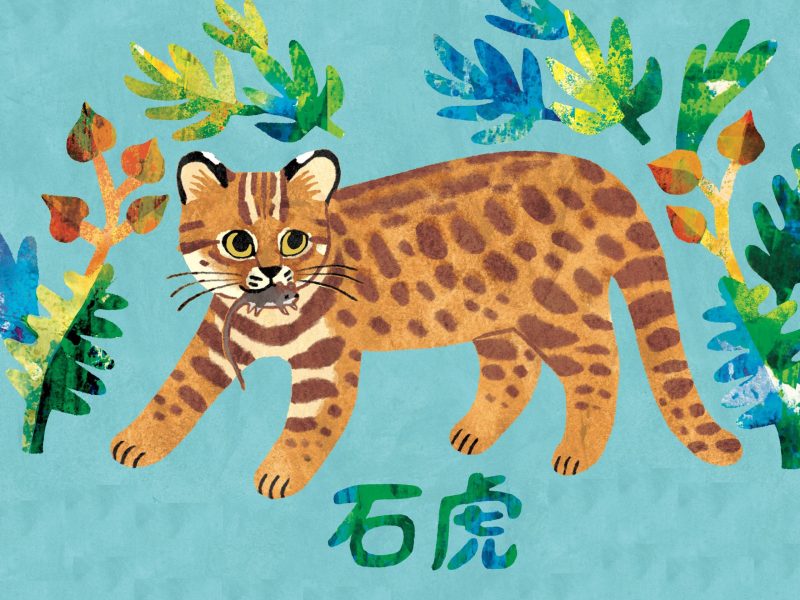土地
最近周遭朋友紛紛出發到日本京都旅行,賞櫻名所清水寺無疑是大家的口袋名單。對我們來說,清水寺是搭飛機才能造訪的古剎,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早在一百年前,臺灣就與清水寺有了連結,不必飄洋過海也能參拜清水寺觀音菩薩的分身。日治時期,移居臺灣的日本人為了求保佑,將故鄉的信仰帶來臺灣。這些神佛,有的是單一神像,也有石佛組成的靈場,好讓他們就近巡禮。
不似多數菜市場周邊通常有的舊氛圍,文賢市場緊鄰大路和眾家連鎖店,改建不過二十多年的市場,還有一塊專屬立牌,呆板藍底掛上金色黑體字,若非寫的是「岡山文賢市場」,還以為是哪個公家機關辦公室。當地朋友說,文賢市場是岡山的命脈,我想是的,光市場旁的維新路,就擠了好多顆心臟,要是大家的脈搏可以被聽見,我恐怕是會耳聾。
從大溪川回來後,我整理了照片,打開圖鑑,翻到明仁枝牙鰕虎(Stiphodon imperiorientis)那頁。「明仁枝牙鰕虎,別名東方帝王、帝王枝牙鰕虎。屬於兩側洄游性魚類,通常出現於清澈的小溪流中,但以中下游較為常見。」我翻閱圖鑑,瀏覽照片,讓知識在我的經驗裡發芽。「具底棲性,為底棲性魚類,不好游動。食性以藻食性為主,亦以浮游性生物或小型的水生昆蟲為食。」
隨著漸暖的天氣,我開始動手整理囤放在倉庫的纖維原料,為了延長使用年限,需要定期做好防潮、防蟲、抗菌等措施,以利存放。趁著午後好天氣,我將絲瓜絡整齊排列於門口埕(mng-kháu-tiânn),讓陽光中的紫外線幫忙殺菌、除濕,最累的就是要定時翻轉,以免晒不均而生黴。
去年聖誕大餐在屏東縣高樹鄉的鹿角蕨溫室裡享用,產地即餐桌,滿滿的田園料理裡有酪梨沙拉、南瓜熬的甜美濃湯,用最新鮮的鳳梨汁舉杯代酒。同桌的農家大哥說,蔬果優質的因素很多,尤其是水,高樹鄉正好被劃為水源保護區。
一道暖陽灑落在金色浪花上,微風吹著沙沙作響的玉米葉,如同黃金般耀眼奪目,當我還沉浸在暖陽微風的美好光景,背後卻傳來一陣疼痛,「你要玩到什麼時候?趕快採一採,等一下收割機就要來了!」媽媽趁我摸魚的空檔從背後猛然一拍,嚇得我往前踏了兩三步,回:「我才剛停下來,哪有玩……」手裡拿著鐮刀,將玉米一穗一穗往茄芷袋裝。
依稀記得小時候逢年過節,就會聽到媽媽與電話另一頭的外婆討論著今年種多少棉花、可以打出幾斤棉被、數量不夠要拿舊的棉被去補斤數……一番討論後,媽媽掛上電話轉頭對我們說「假日不能亂跑,要去田裡幫阿嬤採棉花」,便打給棉被工廠敲定時間,否則越靠近年節,打棉被的人變多,工廠幾乎天天滿班,萬一排不進去,只能將就蓋舊棉被,等過年後才能去打一床新的。隨著阿嬤年紀漸長,自己種棉花打棉被的生活場景也隨之消逝。
在我所受到的訓練裡,只有拍到的魚才算數,證據的形式必須是影像,唯有這樣才能使人採信。至於那些在能見度之外的、躲進石縫裡不見的,因為各種亂七八糟的原因沒拍到,結果在茶餘飯後被拿出來吹牛的,充其量只能算作傳說。
「新正玩三天,上元玩三暝。」澎湖人過元宵比過年還熱鬧,小島居民稱元宵節為「上元」,不同於過年到初三的白天走春拜年,從正月13日起的春節尾聲,人們連續三個晚上為了慶祝元宵而忙碌,各大活動都在夜裡展開,尤其是外垵的溫王宮最為熱鬧。
我們提著燈走入漆黑的洞穴,洞內積水深度及膝,水珠從洞頂的石壁滲出,長出一條條鐘乳石。原本以為小小的洞穴,沒想到隨著我們的燈光不斷往前延伸。突然燈光外圍的黑暗中一陣騷動,幢幢黑影倏地朝我們襲來──原來是棲息在穴底深處的蝙蝠。
記得某年秋天,我為了追蝶跑到新北三芝的青山路,發現濃密森林下方有條山徑,入口指標寫著「紅葉谷瀑布步道」,我好奇的往內走,突然看見很多片枯葉在林中飛起,原來是枯葉蝶!這是我遇見最多枯葉紅葉谷追尋枯葉蝶的地方,往後這條步道成為我經常探索的生態祕境。
沿著莒光路往靈濟古寺而去,是金門最繁鬧的中心。如今,穿梭往來的泰半是尋訪古蹟或美食的觀光客,對照攝於1958年的黑白照片:八二三砲戰不久後的後浦大街上,趁著不打砲的雙數日〔註1〕上街採買的阿兵哥們,才是被鏡頭捕捉到的多數主體。
秋冬最令人身心舒暢的事,莫過於泡溫泉了!新北市烏來區是北臺灣的溫泉勝地,也是生態豐富的物種基因寶庫,烏來位於大臺北地區的水源地,有南勢溪與支流桶後溪、內洞溪、大羅蘭溪、扎孔溪等流竄,到處可見飛瀑流泉,茂密森林孕育了豐富生態,不少生物都以烏來來命名,例如烏來月桃、烏來柯、烏來杜鵑、烏來捲瓣蘭……不妨走一趟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一窺堂奧。
偶爾在南部發現鄉間小廟,先別急著認定是土地公,仔細瞧瞧,有可能是統稱為「五營」的神將。不要小看這小巧的廟,裡面可是擁有千軍萬馬神力,守護村莊不受邪魔入侵,是村裡的捍衛戰士,在臺灣南部與金門、澎湖為普遍的民間信仰。
好久沒逛這麼擠的市場。還不只擠一下下,室內擠到室外,馬路擠到巷內,「公有崇德市場」和「民有崇德市場」相連,導致臺南市東區、文化中心後頭這一大塊地,每天早上都水洩不通。跟人擠就算了,機車也擠過來,阿姨拍拍我的肩:「妹妹,我車停在妳後面,要小心欸。」我一轉頭,後照鏡挨著我的背不是啊,為什麼我要小心?阿姨妳車騎進來室內市場是什麼意思!
「如果你住在沒有經過人為破壞的森林裡,那你一定可以在生活圈中找到滿足所有生活需求的植物,只是你認不認得而已。」最早引領我進入植物世界的老師曾這麼跟我說過。後來我確實發現,日常中每項需求的空缺好像就這麼剛好會有一個植物填補,而每一種植物都可以講出一個完整的故事──就像我最常拿來取纖編織的夥伴:山芙蓉。
馬祖今年的涼意特別晚到,中秋過後一個月,才終於要添一件抗風薄長袖。由於地形起伏大,在地人多以車代步,四季分明的天氣卻常常讓機車族煩惱──35°C高溫的夏天,午後到傍晚短短的時間內,機車置物箱就可能有蜘蛛結網;冷到會下雪的冬天,只要三五天沒騎機車,發動時間就有得等。至於春天的馬祖呢?常常午後陰雨不定,空氣中充滿溫濕氣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