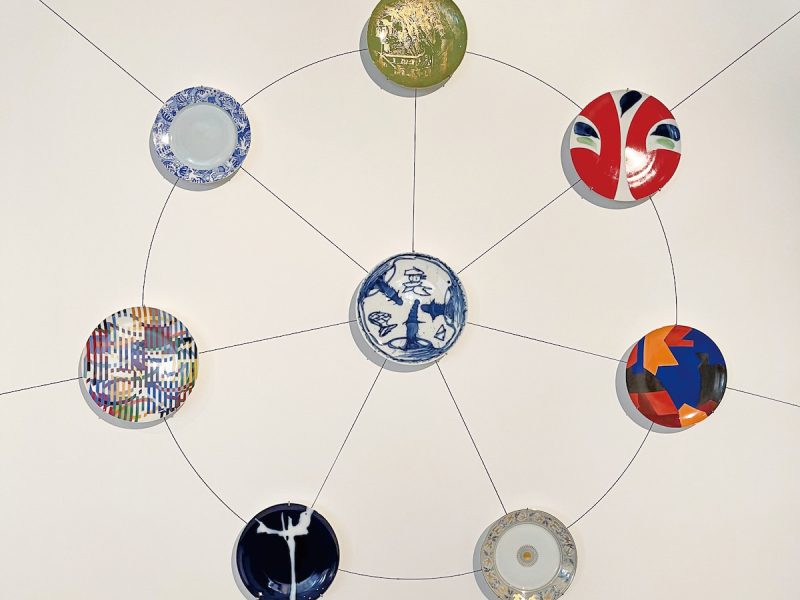飲食
農曆七月是俗稱的鬼月,民間相信鬼門開期間,俗稱好兄弟的孤魂野鬼來到人間「放假」。普渡現場會準備很多好料讓好兄弟飽餐一頓,其中有一碗神祕的湯,湯裡只放了空心菜,看似平平無奇,卻是人們款待好兄弟的暖舉。
空心菜湯是為好兄弟特製的,雖說是湯,但沒有任何調味,不加蔥蒜,不打蛋花,只用熱水稍稍燙過,有些地方甚至不切段,直接使用整把菜浸在湯水中。
小時候,媽媽夏天常煮薑番薯甜湯,用電鍋煮一大鍋,說是喝了消暑,為了養生,只加很少的糖,完全不甜!我不喜歡番薯煮完淡而無味又粉粉的口感,對這道甜品興趣缺缺。
長大開始追查飲食文化的線頭,發現臺灣民間有一道治中暑偏方──黑糖水加番薯粉。用冷開水將黑糖粉和番薯粉泡開、攪勻,喝下去,能緩解暑熱造成的身體不適。
日前,如「喜相逢麵館」這類家宴型餐館話題聲囂塵上,許多人對於它能得到富豪、名人青睞而感到不解,事實上這類餐館在臺灣存在已久,並非近年才開始走紅。
一、二十年前臺北就有「歐家宴」、「煉珍堂」等,「明福台菜海產」就更早了,已經四十多年,贏得「富豪餐桌」之稱。家宴型餐館破除了幾個常見餐飲迷思,我認為那便是受歡迎的關鍵密碼。
每年夏天,是英國盛產草莓的季節。與臺灣常見的淋煉乳吃法不同,英國的草莓除了直接吃,其他常見吃法還有撒點砂糖、淋淡奶油,或是做成簡單的夏日甜點,甚至沙拉。一路吃到夏季尾聲,隨著最後一盒寫著英國產的草莓在市場消失,日照漸短又開始陰雨發冷,就知道夏天真的結束了。
充滿草莓香與陽光的英國夏天,明明早已不像孩子有暑假可放,心情還是會不由自主的放鬆起來。
各式各樣的歡樂時刻,總少不了一盤讓人看了心情就好的Eton mess(伊頓混亂)。
「我有准妳拍照嗎!」雜貨店老闆從櫃檯前一路罵出來,蹲在地上挑蒜頭的客人,掀起口罩悄悄對我說:「妳別介意,老闆很嚴肅。」這種情況下,要我對老闆說出「因為門口春聯字很美」都開不了口。
「西港市場」在當地大廟「慶安宮」的對面,探索的開頭便來這麼一記,挺讓人沮喪。踏進市場,發現半數攤位跟我的心一樣已經打烊——不,是根本沒開,剩餘幾個肉鋪子,在八點鐘就清閒得彷彿將收攤。
第一次拜訪位於北埔老街上的「寶記茶舖」。此處觀光氣息濃厚,人群往來、熱鬧不減,顯現老街的生命力依舊盎然,不少店家都讓人流連忘返。
因工作關係,有時會到竹東一帶,卻未曾踏訪北埔的任何一間茶行,不熟識之外,也對東方美人的價格年年高漲感到卻步。恰巧有次朋友同行,臨走前,跟我們推薦這間茶鋪,當時的他,試喝一輪後,也買到喜歡、價位可接受的好茶。
因為層層不可細數的緣由,麵食一直在我行動菜單上,有一席之地。記得那時於嘉義民雄求學,在家庭與學院往返,民雄車站是中繼點,往右是陽光空氣震蕩的學術之旅,往左便是均衡身心的小吃集散地,日子就這樣一天過著一天,火雞肉飯、鐵板燒、芋圓、當歸麵線,一家替換一家。
「椪皮」就是炸豬皮,閩南語辭典寫為「磅皮」(pōng-phuê)。民雄椪皮麵的椪皮,是將炸得脆爽帶勁的肉皮滷得入味發亮,以取代肉。
初夏,市場一片黃澄澄,金鑽鳳梨上市,臺灣果然是流著奶與蜜之地,活在能大吃鳳梨的地方太幸福啦!
幼年時不太敢吃鳳梨,酸香迷人,但多吃就咬舌。鳳梨咬舌是因為鳳梨酵素豐富,能分解蛋白質、軟化肉質,換句話說:當你在吃鳳梨的時候,鳳梨也正在吃你。為了防止這種吃與被吃的無限輪迴,臺灣農產品改良開發到達了神之境界。現在市面上各式鳳梨品種甜度驚人、各擁奇香,纖維柔軟,更不咬舌。其中最平價廣受大眾喜愛的,恐怕就是金鑽鳳梨。
日前在臺北參加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餐宴活動,名為「起司復刻宴」,尚未入座,便看到桌上一盤羅列不同品項的起司,這盤起司不只形狀,顏色、質地、風味也各異其趣。
這場活動的主辦人,是臺灣第一家義式手工乳酪坊「慢慢弄」的負責人陳淑惠(Isabella Chen),她邀請鑽研中國古代菜譜的美國歷史學者董慕達(Miranda Brown),分享古籍裡出現乳製品的菜色,並由臺中「Restaurant le Plein滿堂」餐廳主廚林凱維復刻重現。
我的臺灣夏天記憶,是吃完外帶的剉冰後配著冷氣隆隆聲睡午覺。酷暑中從有冷氣的這家店再到也有冷氣的另一家店。西瓜、芒果、思樂冰,吃到身體發寒。
臺灣的夏天不缺熱度,反而讓人更珍惜冬天的冷。到了英國則是相反,到了四、五月發熱衣都還穿著,等真正開始熱起來,也不過就是那兩個月的事。
在英國,夏天一到我就會往海邊跑。大概是六、七年前開始,每年天氣一熱就會去濱海小鎮Whitstable,抓螃蟹吃生蠔。
善化人我,只熟家鄉鄰近兩、三區,地理位置再向外推一圈,則非常陌生,因此今日前往佳里區時,還想它或許地處偏僻,頗有預備探訪鄉間之感。
豈知,剛抵達位在佳里中心地帶的中山市場,立刻脫口而出:「好……強……」自此,「好強」二字不離口,臺南市五處百年市集,唯一位處市區外的,便是中山市場,兩百多攤全年滿租,在這也無節慶的平常日,便滿場吆喝。百年市場,不乏光復初期開業的米苔目、七〇年代起家的肉圓。四十年歷史,幾乎要是此處店家的基本盤。
我對食物有些小小執念,像是吃慣了澎湖麵線,就不太能接受其他軟軟爛爛的麵線。除了口感差異之外,最特別的便是澎湖麵線入口前的那一股鹽水香氣,很是誘人食慾。
「海風鹹鹹,晒出來的麵線不用加鹽」從小聽著阿嬤叨唸,一直以為是老人家節省,直到長大自己在臺北的小廚房開伙,被母親耳提面命煮麵線不要再加鹽,才知道煮澎湖麵線真的不用加鹽便已有滋有味。
阿伯的本名顏永興,跟我父親是同輩的親戚,因為要寫茶專欄的機緣,在父親居中聯繫與陪同下,終於第一次見到這位長輩。
阿伯的茶園總計約有三甲,分散在石碇區的幾個地方。拜訪當天,他帶我們彎入水底寮的一個小岔路口,看看其中一處離路邊比較近的茶區。為了改善土質,阿伯使用合法範圍內的有機肥,主要成分是米糠跟麥麩。
問到阿伯當初是怎麼想要種茶跟做茶,阿伯說:「原本是看到自己的爸爸做得很辛苦,想幫忙,後來對茶很有興趣。」
久聞東埔愛玉亭大名,但那次我和兩位朋友相約從東埔攀登郡大山時第一次到訪,早上還不到七點抵達登山口,看到斗大的「古道愛玉亭」招牌,還有老闆娘中氣十足的吆喝聲,我才知道原來這家小店這麼早開。
我們的行程避開了車程遙遠又顛簸的郡大林道,捨棄傳統的入門走法,選擇從東埔爬升超過兩千公尺的「硬斗」路線,預計要在山上紮營兩天,回程則下開高山接回東埔開高巷,走一條小環狀路線。當時不確定幾時才會下山,所以我提議,先吃碗愛玉再上路吧。
對於一部分的老臺南人來說,鱔魚意麵是最有歸屬感的食物。
這麼多年來,很少在臺南以外的地方,吃到真正的鱔魚意麵。因為那必須得是鮮脆滑嫩的鱔魚,配上金黃色的意麵體,融合酸甜的勾芡醬汁,一起入味;抑或是帶有熱騰騰鑊氣的乾炒版鱔魚意麵,用大火加上蔥蒜等佐料爆香翻炒,看食材在鍋裡跳躍滾動,和火焰共赴一場地方盛宴。
小時候阿公很愛帶我從西子灣的渡船頭搭船去旗津,有時中午太熱就吃大碗公冰當午餐。從港務局退休的他曾告訴我,以前大碗公冰那邊是製冰廠,沒什麼錢的水手就自己帶著碗公去冰廠裝冰消暑。後來那一帶就自然開起了冰店,而且越做越大碗,巨大的碗公盛著尖尖的「冰山」擺在桌上,硬是比坐著的你還高上一些。
看著「滿山遍野」的水果,你心裡有了與平時吃冰不同的感受,此刻你彷彿成為一個挑戰者、登山者,要靠著撿拾路上的水果來征服這座五彩冰山。
梅雨一過,隨即迎來燠熱的夏天,市場上的水果品項一變,梅子、脆桃與桑葚消失無蹤,碧綠如寶石的青芒果卻悄悄上市了。
詩人余光中曾寫詩頌讚寶島的芒果如何熟甜、腴美,使中年的他甘冒被妻子責罵的風險,打開冰箱偷吃最易上火的芒果—─「但一切已經太遲了╲懷著外遇的心情,我一口╲向最肥沃處咬下」,冰透的芒果當然好吃,詩中以美女艷紅豐隆的體態比喻芒果的誘惑,歌頌的是熟女之美。
在江浙餐館裡,一翻開菜單,便能見到菜色裡有「火腿」的蹤跡,像是蜜汁火腿、醃篤鮮、火腿蠶豆……用到陳年火腿的比例特別高,幾乎成為江浙菜的重要識別之一,只是不同菜色需求的火腿熟成程度不同,有的用「家鄉肉」(新腿)、有的則用陳年火腿。
有句話說:「唱戲的腔,廚師的湯。」不同菜系會用不同湯頭烹製菜色,江浙菜則會用金華火腿、老母雞熬煮成奶白色的金華火腿雞湯。
讀哈利波特的時候,常常看到裡面提到乳脂鬆糕。照字面上來看,很難想像到底是什麼樣的食物,曾以為是一大塊鬆鬆軟軟加上鮮奶油的蛋糕。到英國之後,才發現Trifle的真面目與鬆糕並無太大關聯,而是一種放置在透明容器內,由各種食材層層堆疊而成的豐富甜點。
剛開始與Trifle的相遇並不算浪漫,我灰頭土臉、飢腸轆轆的從學校回家,照常去宿舍附近的Tesco(平價連鎖超市)買晚餐食材,瞥到裝在透明大碗公裡的Trifle正好打折。
南門市場與我,經常保有一種亦近亦遠的關係。大學讀戲劇系,不時要到國家戲劇院看戲,與其相對的南門市場門面,再熟悉也不過了。然而自從有次入內逛了一圈,被物價嚇到的大學生,從此只上二樓吃「合歡刀削麵館」。
日治時期建起的「千歲市場」,歷經多次改建,在戰後更名為南門市場。自中國遷來的住民,將家鄉味帶來,各省老字號店家在此雲集,南門市場扎扎實實成了中菜基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