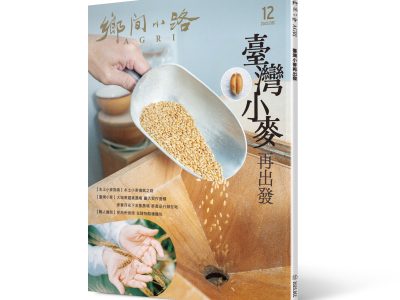文字╱攝影 張曼娟
緊張忙碌一整天之後,想要放鬆的途徑往往是最不健康的,像是鹽酥雞,或是喝啤酒配熱炒。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,毫無懸念,當然是鹽酥雞與一切鹽酥食材,但若是幾個人一起,就會走進熱炒店。我和工作夥伴選了幾道菜,而後瞄到四季豆,老闆說金沙四季豆不錯喔,就是它了。那晚的餐桌上,最受歡迎的確實是帶著點焦香氣味的金沙四季豆。許多的蒜片和蔥花,炸過的鹹蛋黃與四季豆,連掉落的屑屑都好吃。我們很快將菜一掃而空,服務生來收盤子時,我聽見同桌夥伴喊了一聲:「等一下。」迅速將盤子裡剩下的蔥花全數撥進飯碗,而後心平氣和的說:「可以了。謝謝。」「如果還想吃的話,我們再點一盤呀。」我看得有點過意不去,夥伴搖頭:「不用,最好吃的就是這個呀。」
我驀然想起廣播電臺的同事小佩,每當我們去餐廳吃飯時,只要菜餚上點綴著蔥蒜,大家就會起鬨:「哇!小佩的最愛來了。」不管是路邊小吃或是米其林餐廳,對小佩來說,蔥加蒜就能令她笑逐顏開,雙眼發亮。有人這麼愛吃蔥,我也遇過一點蔥都不愛的朋友,哪怕只有一點點,也要挑得乾乾淨淨。
我家的蔥油餅曾是親友間傳頌的麵食,與韭菜餃子齊名。父親會去豬肉攤買來網油,處理乾淨後剁碎,鋪在自己擀製的麵皮上,再密密撒上青蔥和鹽,而後攤在鐵鍋裡慢慢煎。網油化了浸潤著蔥,鹽味均勻,香氣撲鼻。我家的蔥油餅是薄的,煎到呈現半透明狀態就出鍋了,一口咬下去,香酥脆的口感,總使人忍不住吃得太多。自從父母衰老之後,張家蔥油餅就成了絕響。父親的最後三年,我怕他整天閒著沒事做,便慫恿他到我們小學堂來教授蔥油餅。母親聽了倒是興致勃勃:「可以可以,這個我會做。」等到他們來到小學堂,失智的母親坐進沙發看報,再也不起身了。「妳可以教我們揉麵呀。」我央求她,她繼續看報:「我哪有力氣揉麵啊?我在這裡休息,你們去忙吧。」父親發現我沒有買到網油,只能將肥肉剁碎,臉色已經陰沉,接下來進行的都很不順利,張家蔥油餅到底是失傳了。
小時候不管是紅燒魚還是乾燒蝦,總要放上幾段蔥,紅通通的醬汁和綠茵茵的蔥段,光是配色就很有食欲了,在醬汁中煮軟的蔥特別好吃。當我蒸好魚,將蔥絲盤好,熱油澆上,發出霹靂的清脆響聲,莫名的興奮感從心中升起。俗諺有云:「正月蔥,二月韭。」正月是吃蔥的好時節,為了多找點機會吃蔥,我會煮上一鍋雞湯,切大量蔥花撒入,像一方長滿浮萍的池塘。或是切了薑末與蒜末先入油鍋小火炒,再切許多蔥花,將蔥白炒軟了再放青蔥的蔥花,略炒幾下,便加鹽與白胡椒粉調味,而後熄火,放涼了裝瓶,靜置冰箱。拌麵、拌飯、沾白斬雞或烤肉都好好吃。

作者 張曼娟
中文博士與文學作家,悠遊於古典與現代之間。近年以中年三部曲,開創中年書寫新座標。喜歡旅行、料理、觀察、發呆。最新飲食散文《多謝款待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