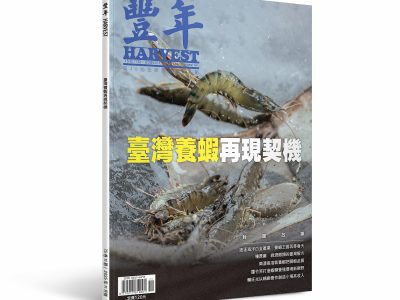文・圖╱喵球

1982 年生,現職地上空少(廚師)。上班常利用休息時間寫詩,因為上一秒通常都還在煮菜,所以寫詩的時候常寫到手指抽筋,也常因為抽筋的疼痛忘記自己本來要寫什麼。出過幾本詩集,銷量加起來破1千本。詩集《4歲》曾獲楊牧詩獎。
青年詩人喵球長年從事餐飲、廚師工作,在COVID-19疫情期間報名青農培訓班,隨後在友人協助下成功承租田地,克服新手務農的現實門檻,以兼農形式投入玉米、玉米筍的有機栽培。從「無法想像自己務農」,到「感覺農業作為一種生活型態的醍醐味」,這段從農經驗平直地抒寫對於作物生命力、大自然生態的感性,也含蓄地點出有機栽培推廣的難關。
我其實沒有辦法想像自己務農的樣子,特別是在上過青農培訓班課程之後。
那時我在桃園機場第二航廈的餐廳工作,因為COVID-19的關係機場每天空無一人,那家店很快就歇業了。我一邊煩惱疫情期間工作難找,一邊注意到桃園青農培訓班如期開辦的訊息。那是個為期半年的有薪輔導課程,我抱著碰碰運氣的想法用岳父的地契報了名。報名的過程也產生了第一個了然——「原來青農輔導並不是鼓勵任何一無所有的青年從農,而是鼓勵親戚朋友有農地的青年從農」。日後我才真正理解,這其實是非常實際的考量。
幸運地報上培訓班在第一次課程後,我更不能相信自己務農的樣子了——班上同學不是農二代,就是本來就在務農的人。我們以往在報導中看到的那種「放棄高薪工作下鄉務農」的人物奮鬥故事,終須一個現實的前提——他得有地能耕,地若不夠大,還保不了農保。因此對於一般有意創業的青年而言,農業就和絕大多數產業一樣,不是能輕易相信願景的選擇。即使在完成3個月的室內課程,並開始在農場的實習課程後,我仍然無法想像自己務農的樣子。

有地有人脈 等於進場務農的保證
我實習的地方是以溫室栽種小松菜為主的傳統農業農場,因此田裡幾乎沒有蟲也沒有雜草,最常做的就是拔菜。通常拔菜時土壤的溼度控制得也很好,從菜莖底部一拉就能連根拔起,再稍微抖一下,菜根看起來就很乾淨了。跟我原來的廚師工作相較之下,整個實習過程意外地舒適,對身體最折磨的大約就是以蹲坐為主的下盤動作。
一個人在溫室裡拔菜,感覺菜葉上可觸摸得到的生命力,不免使人想起一些關於土壤中益菌與人類心理健康的報告❶。或許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感性,但我認為務農,在土壤上與植物一起工作就是能給人一種不可言喻的踏實感。不過,我仍然沒有想像過自己務農的樣子。在整個課程結束後,我又找起了廚師工作,但不久便透過青農培訓班的學長介紹,認識了桃園市觀音區某社區總幹事,並在其遊說之下取得了1甲地的耕作證明。
在大園觀音一帶有許多看起來沒在耕作的農地,大部分地主聽到有人想種點東西都算樂見其成,畢竟耕作包含了農地管理,但一聽見要打租約、要簽名,態度就變了。「只要不打約都可以,要種什麼隨便你。」後來得知,這是「耕者有其田」❷等土地政策帶來的後遺症。後來總幹事出面掛保證,地主們便同意簽名,我才知道為何農業課程一直隱約在強調產銷班、人與人的交流。畢竟對我來說,種地多少與「隱世」有著浪漫的連結——應該也是有人就想安靜地當個I人(introvert,內向者)才來種田,怎麼又要培養人脈又要加入產銷班了呢。

抗雜草逆境 神一般的作物玉米
有人幫忙解決了耕地的問題之後,我也就順理成章地開始種田。那時我與太太接受了農友的建議,以中美洲阿茲特克傳說中羽蛇神帶到現世的奇跡——玉米為主要標的作物。它本身具有耐旱、好照顧的特性,在不良的氣候與水土管理條件下雖然長不贏雜草、營養不良,但其實仍會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自行在雜草叢中默默生長。
玉米是阿茲特克人極重要的糧食作物,玉米苗也是玉米女神(Chicōmecōātl)的象徵❸。如果你有機會到大園走幾趟,你會發現一些平常沒在種的荒地,會忽然請人來耕,沒隔幾天忽然整齊地種上了作物,不是火龍果就是玉米,那就是為了「視察」(需證明農地有在耕作)而種的。看那些在視察後便無人照顧的玉米,終究還是在雜草中長起來了,真會覺得玉米是種神一般的作物。

在當代農業中,玉米可能是蔬菜也可能是糧食作物——玉米筍被歸類為蔬菜,而玉米則是糧食作物——這冷知識般的特性,在申請轉作補助時可是極為便利的。而在看著玉米抽芽、長高、結穗成玉米筍、再從玉米筍充漿為玉米,我也才對玉米筍就是「玉米嬰」這件事有了完整的理解。我想這就是《新世紀福音戰士》裡加持良治說過的「培育東西的充實感」❹,這種充實感來自知識轉化為生活經驗的瞬間,也來自一個人真的在世界上種出了生命的基本需求。
我的第一期栽種可說是非常失敗的,由於一邊上班一邊種田的關係,經常遇到好天氣要上班,放假卻又下雨無法打田的狀況。我的農場當時是以有機農業為目標,使用的工具只有中耕機、割草機,主要的除草方式就是藉中耕機打田覆土。這種除草方式非常看天,土要乾,中耕機才能在田裡順利運作,但田裡排水沒做好的話,就算雨後一週土也不會乾。這時如果不信邪,硬是把中耕機推到田裡打土,就會看見中耕機刀片在旋轉中逐漸變成一個大泥巴球,你會覺得自己就是隻堆糞蟲。
只要在雜草剛發芽的時候遇上雨天,沒能及時以中耕覆土的方式除草,後續就只能勉強以手工除草,或者看著雜草與標的作物爭高了。由於我一開始對田的排水真的沒什麼概念,雨後幾天我都只能背著割草機在田裡加減除草。而即使有了機器輔助,人類要對抗雜草的成長速度還是太難,最後我只能安慰自己,「沒關係,我這是不除草的自然農法啦!」
就這樣,等到第一期耕作的玉米收成,我甚至忍不住自己黜臭(thuh-tsháu),「這樣也能長!玉米也太強了吧!」一邊讚嘆一邊將及腰雜草撥開,並採下生命力不亞於雜草的玉米,真的可以理解為何有些人認為玉米就是神。



螢火蟲回歸 見證大自然恢復能力
當時COVID-19防疫正是最嚴格的時候,許多人搶買物資、口罩,並為長期的居家防疫感到焦慮。而我就是載著農具到田裡,脫下口罩與土壤、雜草、玉米跟昆蟲待在一起。有時帶小孩到田裡踩草、抓蟲,竟也補足了小孩在疫情期間無法外出遊玩的遺憾。雖無法販售賣農產品維持生計,但也感覺到了農業作為一種生活型態的醍醐味。
那時我主要的農產販賣方式是以地方團購群組為主,湊滿500元就送貨。也許因為疫情經濟,或當時青埔一帶的生活機能尚未完整,有機農產比我想像的還好賣很多,那時常常是採不夠賣的。此外當時也接過超市的單,但要出貨到超市必須自行理貨包裝,還可能被退貨,對小農而言負擔較大。幸好那次沒被退貨,因此也不曾擔心過農產滯銷的問題。
在種到第三期時,我終於遇到一回天時地利人和的收成,整齊的玉米植株、稀疏的雜草、鬆軟的泥土,採收那塊田的感覺真是千滋百味難以言喻。而我也在田裡看到幾回螢火蟲,讓我非常驚訝——這塊地才有機了半年多,螢火蟲就回來了,大自然的恢復能力原來是這麼強的嗎?要知道,在我的耕地旁邊實行的可都還是傳統農業(慣行農法),田埂光禿乾爽連根草都看不到;反觀我田埂上的草,常常長到經過的老農都要忍住笑。
當然對於多數老農夫而言,雜草就是懶惰的象徵,什麼「自然農法」都只是年輕人的藉口。於是在種了兩年後,地主還是決定將地收回去種稻。現在經過自己曾耕過的地,我也會感嘆,「好乾淨的田埂,好整齊的秧苗,種田還是得這樣看起來才舒服吧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