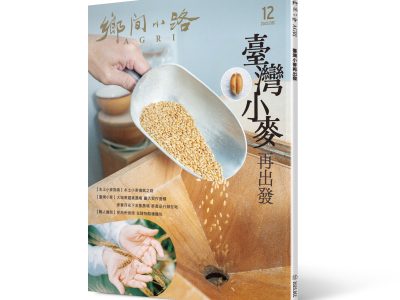文字 林玠芷/攝影 賴力瑜/照片提供 李盈瑩
「每天來菜園不一定是工作,家裡的果皮菜渣,我也會拿到菜園當覆蓋物。」李盈瑩穿著白襯衫、工作褲和雨鞋,戴著草編帽,手拿鐮刀,站在近午的菜園中穿梭、工作,一身優雅乾爽,對照在太陽底下兩小時就像是各自經歷大雨的我與攝影師,她顯得游刃有餘。她的菜園位在灌溉溝渠旁,從草叢中難以辨認的路徑走入,土地分成幾個小區塊,其中兩小塊是鄰居阿姨給她的,「這邊在五、六○年代是養鰻苗的,所以還看得見魚池,產業沒落後,地方居民便在此填土種菜。」


農村生活應該是怎樣的?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醒來就灑掃庭院、餵雞,簡單吃食後投入菜園耕作,鋤草、培土、澆水、採收、整理環境,所謂「鋤禾日當午,汗滴禾下土」,直到夕陽遠遠掛在山邊,天空橙紅,再踩著滿地霞光慢慢回家,每日投入同樣的循環──然而這般刻板印象與李盈瑩的實際生活南轅北轍,「其實我生活有兩種模式,你問的是退休還是趕稿模式?」彷彿湖中女神問你掉的是金斧頭還是銀斧頭,但兩者聽起來和務農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半農半寫作的自在
一九八三年生的李盈瑩移居宜蘭員山已然十年,這段期間她以文字為生,採訪接案之餘亦受邀演講或駐村,同時創作了三本著作:《與地共生、給雞唱歌》、《養雞時代:21則你吃過雞,卻不瞭解的冷知識》,以及二○二四年出版的《彩鷸在家門前秘密遷徙:自休自足X自由接案的躺平日記》,如此多產,究竟住在農村要耕地的自由工作者一日如何安排?
「如果是趕稿模式,我醒來之後會空腹開始工作,因為先吃東西就會悠閒起來,鄰近中午才早、午餐一起吃,吃完繼續工作,下午三、四點的時候若有餘裕,就會在菜園、步道或騎腳踏車三個之間擇一,晚餐後也時常繼續寫稿,就是工作狂狀態。」那,退休模式又是什麼意思?「睡到自然醒之後,我會認真吃三餐和水果,除了照顧菜園,還會打掃家裡、洗衣服、練英文、看書和創作等,沒什麼時間限制。」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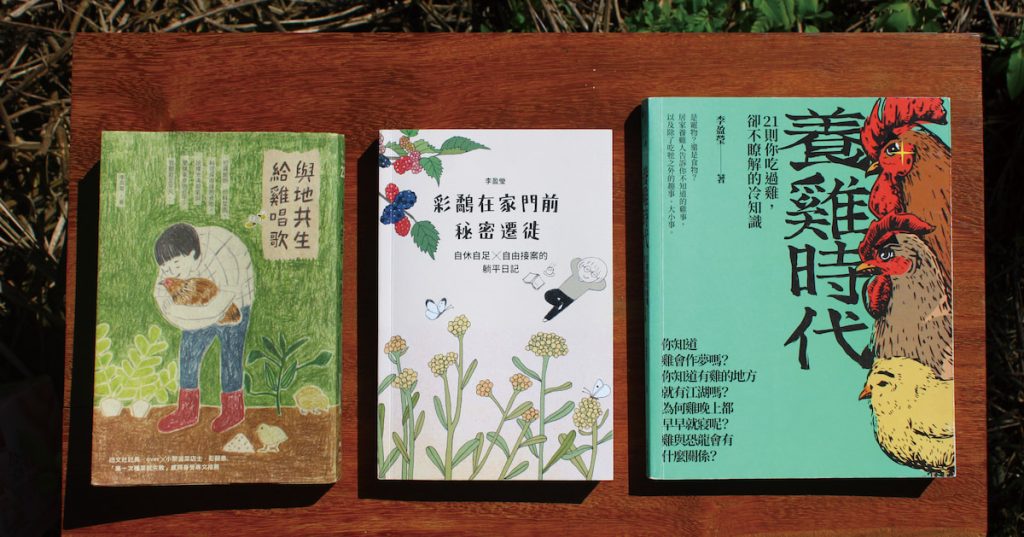
作物找合適風土,人也是
什麼緣分才選擇落腳員山呢?她緩緩說起和此地的相遇,「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多在出版社擔任旅遊記者,走訪臺灣各地,看過許多種生活樣貌。」因為工作,李盈瑩曾在花東旅居一個多月,大片的山海與田地,為她埋下日後渴望農村生活的種子。「二○一○年左右我快三十歲,想要嘗試其他方向,在『福山植物園』找到野外助理的工作,負責收集花果和種子。」
當時週間都住在山上,她的作息與山林同步,因喜愛自然,她對這樣的生活如魚得水,「那裡是生態保護區,無人的晨昏,動物們就會出來覓食,看得到獼猴、貓頭鷹和飛鼠等,有一次山羌就在我腳邊吃掉落在地面的橡實!」她的聲音在回憶中甜了起來。
結束兩年在自然中生活的日子,她回到臺北繼續接案,與在大學登山社就認識的黃得恩開始交往。二○一五年,透過員山友人找到現居的房子,兩人決定移居員山,開啟種菜、養雞的生活。

對農村的全部都感到熱戀
「我很喜歡福山那樣自然的環境,也喜歡親近動物,加上我對都市生活沒太多依賴,也認為不需要過度消費,所以農村是非常剛好的選擇。因為有過登山、野外工作的背景,對自然曠野不會有浪漫化的想像。」在這裡生活沒有磨合期,每天都是李盈瑩夢寐以求的日子。只是,這樣子經濟沒問題嗎?扣掉房租、生活所需和保險等等,她說完全沒有問題,甚至有餘。
剛到員山,她和黃得恩兩人存款加起來不到三十萬,但簡樸生活很快就步上軌道,原先空落落的房子小而美,過往植物園一起工作的同事送來客廳的桌子,親戚搬家汰換的沙發床也送給她們;門口放著的,是自己手作的木頭鞋櫃,「我有去上細木作課程,了解木頭手作細節,這種跳過貨幣,用自己雙手創造和解決問題的過程,讓人非常著迷。」他們還報名了宜蘭社區大學「夢想新農種稻班」學習種稻,並結識許多小農好友。
學會種稻後,李盈瑩很快發現自己不喜歡這類農務,「大面積地只種單一作物,對我來說比較無趣。」黃得恩繼續與農友共耕友善農法稻米;她則轉而開始自學嘗試、實驗友善栽種各類作物。「我從農業書籍學習各種農法,從裡面找出適合我操作的步驟執行。比如我會以腐植土育苗,用雜草或稻草蓋在作物土壤上保溼,或運用資材自己設計物理性防蟲方式等等。初期什麼都想嘗試,種過相對冷門的高粱、翼豆、茴香、洋蔥等,但現在會以收成穩定、適合宜蘭氣候、病蟲害少的作物為主,以提高自給率為目標。」





平衡的生活帶來寧靜
移居的第一年,種菜之餘,李盈瑩也養雞,養雞的理由卻不是為了吃,「小雞太萌了!你看過剛出生只有絨毛的小雞嗎?非常可愛!」從打造雞舍、觀察雞的群體生活與生存江湖,到幫雞按摩、準備食物等,她都一手包辦,更為牠們寫出前兩本書。
「第一本書算是記錄剛開始摸索農村生活的狀態,像初生之犢一樣,不斷嘗試與感受許多事物,這裡的一切於我都十分新鮮,也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寫給雞的情歌。」第二本書則是發現,市面居然沒有教人居家養雞的攻略──小雞的可愛,要讓更多人知道才行,決定自己來寫。

李盈瑩說,二十多歲還在臺北生活時,與父母同住,習慣把生活塞得行程滿檔,但依然覺得對生活一無所知;移居後她漸漸感受精神的富足,「真正貼近土地並開始獨立生活,耕作、飼養、煮食、修繕、取材,再回頭從事採訪工作時,能感覺到自己是腳踏實地、扎根生活的人。從純粹的消費者跨足生產者,好像更有底氣去面對外界。」第三本書就在寫這些日常,以更沉澱的心境,談生活與工作的平衡。
被宜蘭山水黏住的生活
二○二三年,李盈瑩與黃得恩登記結婚,到恆春旅居一個月作為蜜月旅行,也是在那時候,她結束養雞。回想起養雞的緣由,除了可愛,還有想要再次感受在山上工作時,那樣被自然和動物環抱的生活,「如今的菜園就像彼時的山林,小雞則是山羌。但養雞和照顧菜園不一樣,菜園放著一個月也沒關係。雞需要每天照顧,或許讓養雞暫停一段時間,才有機會讓新事物進入生活。」她去了宜蘭美術館學捏塑,也嘗試繪畫,希望另闢創作領域,一圓大學時沒能念美術系的夢想。如今她成為新宜蘭人,習慣每年初夏騎車時被烏鶖扒頭、看白腹秧雞穿梭田間,以及曾有南蛇盤踞窗外,還有秋季時,會有山窗螢飛進屋裡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