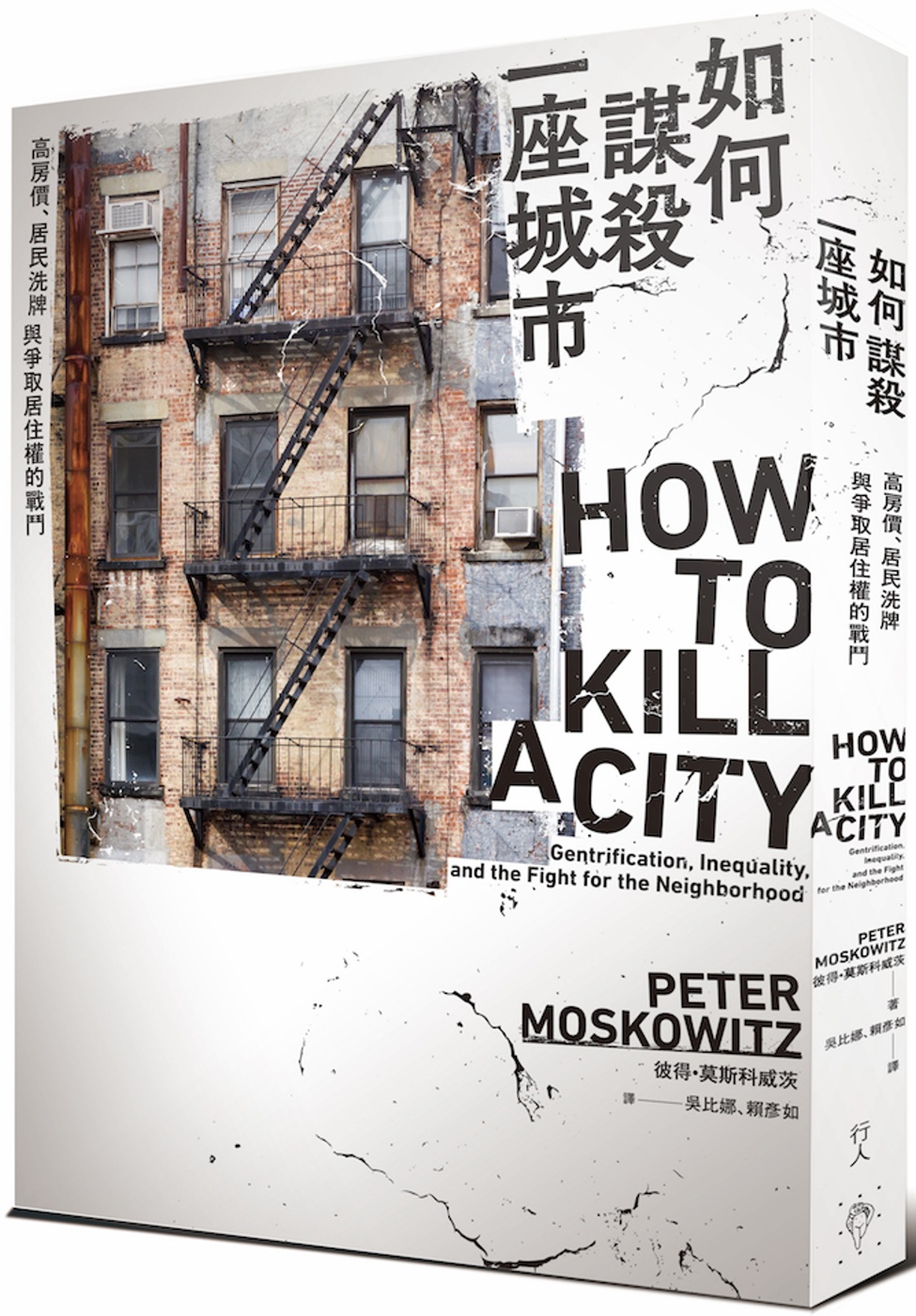內容提供/行人文化實驗室 文/彼得·莫斯科威茨
| 為什麼你該讀這本書
透過一位資深記者於美國紐約等四座城市的探訪與數據調查,探詢社區面臨房價房租飛漲、居民被迫搬遷、社區文化崩壞的過程和背後原因,點出都市變遷背後的政治與經濟之手。如果台灣不停止將土地增值視為首要目標,對房地產買賣仍舊不加限制,社區潰散、住民流離失就是我們自己打造出的未來城市。 |
縉紳化的城市
吉米.菲爾斯(Jimmie Fails)喜歡舊金山:這個涼風徐來、友善,有點古怪的城市。他是戴著毛帽、溜滑板的20幾歲青年,從小在這裡長大,這也是他唯一的生活圈(他曾到紐約住了一年,但恨透了那種孤立和競爭的感覺)。他在舊金山到處有熟人,走到哪都有人拍肩、擊掌,跟他打招呼。
因此當舊金山改變,吉米的生活也改變了,他的朋友搬到其他更便宜的城市,新來的人把他這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當成是外來客。他覺得舊金山越來越不屬於他,自己在其中漸漸像個異類,就像一片殘存的遺跡。
有天吉米決定乾脆把他的生命故事戲劇化,在他朋友的電影裡演出一角。《舊金山的最後黑人》這部影片是關於一個20幾歲舊金山黑人的故事,由吉米擔綱,他們家因為將房屋抵押,繳不出款項,失去了原本大型維多利亞式住宅,他想盡千方百計將它贖回。
把吉米稱為「最後的黑人」當然是誇張了,但是根據舊金山的人口調查,也不算太離譜:舊金山的黑人人口目前只佔5.81%,人數跟1970年代比少了一半,大部份的改變發生在過去20年間。城市仍有很多的拉丁美洲裔和亞洲人口,但人數也在減少。在教會區(Mission),舊金山歷史悠久的拉丁美洲裔社區,拉丁美洲裔人口的比例自2000年以來,已從60%降為48%。如果這個趨勢持續,到2025年,這個社區的拉丁美洲裔人口就少於1/3了。舊金山一度是區域內種族最為多元的城市,但如今卻喪失多樣性,其他的郡、郊區反而增加。到2040年,舊金山的人口會以白人佔大多數。這是城市裡被廣泛討論的話題,如今,若你沒有科技圈的收入程度,幾乎隨時等著準備打包離開城市。舊的舊金山看起來潦倒、脆弱,似乎只等待資本給予最後一擊,讓它壽終正寢。
吉米還能夠留在舊金山,是因為喬的父母─兩個有固定收入的創意工作者,好幾十年前幸運的在教會區的邊緣買了一幢大房子。喬和吉米住在地下室,但他們不能永遠待在哪裡,身為藝術家,他們也賺不到足夠的錢去負擔市區的公寓租金,現在兩房公寓租金的中位數,已經上漲到超過5,000美元。
比吉米年紀大一點的喬,可以指出城市的各種改變:新的星巴克咖啡開張(超過幾十間)、閃亮的高級公寓樹立在老的維多利亞式街屋之間。但讓他們感到最不快的,是那些在蘋果、谷歌、臉書等無數科技公司工作的新居民。他們似乎對周遭的一切無感,穿著polo 衫或襯衫,他們對舊金山來說看起來太一絲不苟了。這些新來的人往往只把城市視為一系列的消費選擇(墨西哥玉米薄餅、啤酒、拉麵、教會區的高級公寓?)而對於每樣東西的獨特性、特殊個性無動於衷。但你可以感覺到,隨著他們一個社區接著一個社區的接管舊金山,這已然成為普遍的趨勢,任何與此不同的事物反而顯得特異。
「這影響到認同,你開始懷疑自己屬不屬於這裡。」吉米說:「他們走路經過我時,甚至不看我一眼。」
有些人會注意到吉米,但卻沒有什麼好事發生,幾個月前,一個白人指控吉米侵入喬父母的房子(他在夜晚以鑰匙打開門)。又幾個月前,吉米在多洛公園(Dolores Park)附近,走在一個白人男子後面,這是一個縉紳化相當厲害的地方,距離喬父母家只有幾條街,這個男子回頭看吉米,可能是害怕被搶,他直直的跑過公園,穿過一排正在灑水的澆水器,讓自己全身都濕透了。
吉米對這些人展現驚人的同理心,他說如果他像他們有那麼多錢,他大概也會這麼做,住在高級公寓裡,試圖躲避黑人。
一個社會運動者告訴我,他很同情那些空降到城市的科技人士,他們為一間小公寓付出前所未聞的天文數字,每天早上7點搭著接駁車被送到帕羅奧圖(Palo Alto),在晚上6點回到家(然後常工作到半夜),搭 Uber 去餐廳吃晚餐,然後下禮拜又重複同樣的生活模式。當然,他們的生活優渥,但也相當無聊,像機械人一樣,幾乎沒什麼好羨慕的。只是令人痛苦的是,他們的出現毀了城市。
對一個外地人來說,我們很難了解舊金山正在遭遇什麼危機,作為一個來自紐約的男同志,當來到卡斯楚街(Castro Street)的同志酒吧,這個地區長期以來是同志族群的基地,我會覺得這個同志社區還蠻不錯的。但如果你過去30年來都住在這裡,你會感到:「過去這裡一向是激進政治行動的溫床,現在卻變成同志迪士尼樂園了。」如果你是我,你可能會逛著教會區(Mission),吃著墨西哥脆薄餅,覺得這個社區看起還蠻可愛的。你不會意識到就在墨西哥餐廳的樓上,一個家庭可能要為一個10呎見方的小房間,付出一個月1,000美元的租金。
我們來到市中心附近的一條巷子裡,距離推特(Twitter)總部幾條街,推特總部因為將總部設在市中心較蕭條的區域,獲得市政府高達5千6百萬美金的免稅額。我開始漸漸了解舊金山所面對的未來,這個巷子看起來就像是城市的留下來的廢墟,骯髒、地板上丟著針頭,聞起來有尿味。當喬跟他的小型拍攝團隊準備場景時,吉米告訴我他的成長經驗:他在一幢大房子長大,裡面有十幾個家庭成員,他的父母因為惹上了毒品問題,失去了房子。自童年起,他在各個出租公寓和社會住宅間流浪,他對舊金山目前的狀況感到極度矛盾。
「我並不是要爭取別人同情,畢竟每個人都在奮鬥求生,」吉米說,「但我還是有種莫名的不安,因為他們把整個文化都毀了。」
在拍攝的過程中,巷子裡一棟建築的窗戶打開了,有人探出頭來大叫:「你們是在拍《最後的黑人》的那些人嗎?」喬告訴我這很常發生,儘管這部電影還要好幾年才能問世,卻已經引起城市的廣大迴響,當地人都知道。我們受到那位打開窗的男人邀請到他家,原來他住在一間大倉庫,建築物被分割為十幾間藝術家工作室,兩個住在那裡的年輕黑人藝術家,艾林.傑佛瑞德(Erlin Geffrard)和提姆.艾瑞史提(Tim Aristil)帶我到處逛逛。工作室裡面一片混亂,傑佛瑞德解釋,這間倉庫已經被售出了,很快就會轉變為科技公司的辦公空間,他和艾瑞史提可能在未來的幾個禮拜內,就得離開城市。
「這一切再也沒有意義了,」艾瑞史提告訴我:「以前你會四處走走,聽到有趣的談話,靈感被啟發,現在到處你只聽到人們談生意,還有這個城市變得多糟糕。」
除了這些無形的改變,工作室也變成貴到無法負擔,傑佛瑞德說他會在東灣(East Bay)找個地方,說不定到奧克蘭(Oakland),艾瑞史提說他可能會搬到洛杉磯,那裡便宜多了,他幾乎所有的朋友都搬到那裡,要不然就是去費城或底特律。《最後的黑人》的拍攝團隊跟這兩位藝術家聊了一會,彼此親切而慎重地說再見。當我跟隨拍攝團隊離開這棟建築時,我由衷希望這部影片不管在評論上和財務上,都一定要成功。我們剛剛見証了兩位藝術家在舊金山的經濟體系被連根拔起,如果這部電影沒有成功,拍攝團隊的兩位藝術家可能也要離開了。